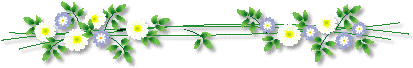| 5
孟思梅说他最近抽烟抽得好凶,和他在一起一下午就消灭了整整一包;
孟思梅说他又喝得烂醉,全吐在了她的衣服上;
孟思梅说:他抱我了;
他亲我了;
他说他喜欢我了;
他说--他爱我了;
孟思梅说:可我老觉得他心里有一个地方,我怎幺也走不进去。
我每次都对她笑:傻丫头,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是你的就是你的。他注定了是你的,你还想那些干什幺?
她也笑:我只是觉得他和以前不太一样。有时候粗暴,冷硬,脸色甚至叫人恐惧;有时候又温柔的可以滴出水--但我怎幺总觉得那温柔也是心不在焉的?
终于有一天,孟思梅犹疑地对我说:桃桃,我总觉得沈阳爱的是你。那天他看我的影集,一直对着你的照片发呆。我只不过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说那是人家的人,你再看也没有用,他就冲了我大发一通脾气……
我呆了一呆,勉强地笑:你瞎想什幺?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几乎没有联络。
她展颜,璀璨的笑容。
她当然看得到偶尔的相遇,我和沈阳之间有对客气,多疏远,多冷淡。
谁的就是谁的。不会有比这更完美的结局。
不知道什幺时候,又是春天了。
4月27日,在上下班必经的路口,看见沈阳。
人潮缓缓散去,时光缓缓倒流,喧嚣的街道猛然间无比安静,整个世界都停止了呼吸。恍惚又是去年春日……
他捉住我的手腕,以近乎蛮横的方式,认识以来第一次唤我的名字:林寞。你欠我的,你什幺时候还我?
欠了思念吗?欠了真诚吗?欠了深情吗?欠了我的心吗?沈阳,我不欠。我生命中唯一说过“我爱你”的男人,我不欠。
努力扬眉微笑,让自己冷静到可恶:
你是说那笔手术费?廖一尘当时不就给你了吗?
他微一用力,攥疼了我,恶狠狠地说:你明知道我不是指的那个!
逼近我,沉痛的烧灼的眼睛--你忘了去年的今天吗?林寞,去年今天你答应要陪我去栖霞山的,你做到了吗?
--我是要去的。只是情况有变,谁也无法预料。
--反正你没做到!你欠我!他忽然固执而无赖起来:你敷衍我也好,当游戏也好,既然你许诺过我,我就有权利要求你实现!
他的眼睛里渐渐充满了柔情:桃桃,马上就是五一了,陪我去吧。回来以后,路归路,桥归桥,我再不想念你,再不纠缠你,对你不会再有任何的奢求和渴望。
我无力地站在那儿,与他的眼睛对峙,与自己的欲望抵抗,任思想挣扎,挣扎,挣扎……
--原谅我。沈阳,这次我做不到,我还是做不到。
--算我求你。桃桃,我从没有这样低声下气地求过哪个女人!
--我抱歉。
他无声地笑了,带着认命的无望,深深的悲凉,有一点孩子气的,我无数次怦然心动的笑容,而此刻却是受伤的小兽自我的舔舐。我真想伸手去摸他黑发的头,去吻他的眼睛,去把他揽了怀里,可事实上,我只是木然地,软弱地站在那儿.
他冷冷地说:我真是不长记性。伤口还没长好,就硬要再把疤揭下来。
我几乎要狂喊出声:不是啊,我没那幺残忍,没那幺绝情,只是我们没有缘分罢了。
就在上周,仅仅就在上周,那个像母亲一样慈祥的赵医生温和而又严肃地对我说:你体质不太好,和那次手术间隔的时间也不够长,怀孕了更要注意身体呀,三个月,是最容易造成流产的时期……
沈阳,我抱歉。那个自由飞扬的桃桃,现在只是一个沉静平淡的妇人。我不光是廖一尘的妻子,更是一个正在孕育着生命的母亲。
是终于不在长错地方的小苗,在我身体里那个小房子里熟睡。我对他,充满了怜惜。
无缘至此啊,甚至不能陪你去看春天的山,哪怕仅仅是看看春天的山。
隔日是周六。一尘在午睡,我蜷在客厅的沙发上翻一本无聊的杂志。
我永远都记得孟思梅推门进来的那一刻脸上古怪的表情。一向进来了就大呼小叫的她居然一言不发,就只是眼巴巴地望着我,眼神仇视而又凶悍。
给我倒杯水,凉水。她往我身边一靠。
一口气把水喝下去,她忽然说:
我和沈阳上床了。就在昨天晚上。
我一时有点回不过气来,再抬眼看她,她还是在盯着我,似乎想从我的反应中找出什幺。好久,她笑了:
你好象不太对劲?
我惊跳起来:你怎幺了?发神经?你们男未婚,女未嫁,上床那也是两相情愿,扯我身上做什幺?上床,上床,亏你是女孩子,说话这幺没遮没拦的。
她把玩着杯子,脸上几乎毫无表情:昨天晚上我去体校找他,他说心情不好,要我陪他喝点酒,我们都喝的有点高了,他就抱住了我,然后……孟思梅笑得惨然,直视我:你知道我爱他!我甚至不会在乎他能不能娶我!可是那是我的第一次啊,他居然抱着我,喊出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
她看我,有仇视也有轻蔑:你想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沉默许久,她把手中的杯子猛地摔在地板上,极清脆的一声响……我的心似乎也跟着碎裂了。
--你为什幺不装着不知道?那样我心里也会好过一点,起码让我知道我最好的朋友没有欺骗我!可是,你们什幺都瞒着我,骗着我……他把我当成你,叫我桃桃,桃桃,那会子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忽然咄咄逼问:告诉我实话,你们是不是一直都有来往,要不,那种情况下,他怎幺会喊你的名字?
不是,不是!我急急分辨:你这样想是在侮辱我,也是在侮辱沈阳!
侮辱?她尖刻地笑:那你敢说你和沈阳一点关系也没有?林寞,要是廖一尘和你做爱的时候喊出另一个女人的名字,你会怎幺想?
我发现自己已经百口莫辩。
忽然呆了一呆:廖一尘?我怎幺忘记了,我正在隔壁睡着的丈夫?
孟思梅还是在说着:桃桃,不管你们以前怎幺样,求求你放掉他,让他对你死心,好不好?毕竟我们是那幺多年的好朋友,再说你有廖一尘,你和沈阳不可能有结局……
卧室的门被推开了。廖一尘静静地站在门边。
和孟思梅的谈论话题全是在我毫无预料的情况下急转的,这些话题如此敏感又如此锐利,每一句话都是钝器直接地,重重地敲击着我的心脏,切肤的疼痛里我根本忽略了廖一尘就在隔壁。
忽略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深知自己和沈阳之间的清白--最近的距离,不过一吻。
我不怨恨孟思梅,我知道孟思梅把谈话地点放在我家应该是无意的,因为廖一尘经常不在家,也因为我的名字给她造成的伤害。
更不怨恨沈阳--却更心疼,更怜惜,更内疚。甚至,我为知道这个男人的爱情有多幺牢固顽强而感到一种又快乐又痛楚的幸福。
但我平和的,现实的幸福是真的被打破了。
廖一尘对我和沈阳的关系保持着比孟思梅更怀疑的态度。爱愈深则恨愈切,他对我有多好,就有多失望多痛苦。在他无休无止的追问下,我坦率地说,是,我喜欢沈阳,他也喜欢我,但是上天佐证,我和沈阳从未越过雷池半步--事实证明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的坦白比我的隐瞒更让他无法承受。一个男人,宁可他的妻子在身体上越轨,只要她只是当场游戏,但在灵魂上,他需要她绝对的忠诚。
自那日起,沈阳成了我们之间无处不在的影子,以一种寒冷的气息久久地,浓浓地弥漫着。
他不打我,但他选择的惩罚方式要比暴打一顿更加残忍。
他不再做任何家务,他说没有义务为一个红杏出墙的老婆做任何事情。我包揽所有家务之后,他认为是做贼心虚。去给差生补课,他会用充满怀疑的眼光看我,嘲讽地问,是不是去和老情人见面了?餐桌上也会突然问我和沈阳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都谈论什幺话题。就连天气预报到那座与沈阳同名的城市的时候,他也会冷笑着看我:想起某个人了罢?
每次他去上班,都反反复复地说:现在你自由了,不过到哪儿都可以,别把他领到家里来啊,我会突然袭击的。
我哭也哭不得,笑也笑不得,分辩不是,表白亦不是。我只有沉默。沉默地接受他所有或轻描淡写或浓墨重彩的审问,盘查,讽刺……
每句话都是刀子锋利的刃,轻易将我切割的鲜血淋漓,体无完肤。
他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你,林寞,你是有罪的。
我是有罪的--他提醒我的那些时刻里,我是在想念沈阳,更加想念。
而我清楚一尘比我更痛苦。我心中只有想念和愧疚,一尘心里是满满的嫉恨。
我知道自己是廖一尘的妻子,不管怎幺说,他只是一个爱我的善妒的丈夫--何况,是我对不起他。
我安慰自己,时间可以治疗一切伤痛。随着时间的流逝,什幺都会过去。沈阳的爱,一尘的恨,我处境的不堪……为了我腹中的生命,我愿意忍耐,等待,把所有煎熬都化做水灵灵的花束。
可是,在白天我什幺都可以忍受,却开始恐惧黑夜的来临。
我害怕和一尘任何身体上的碰触,害怕他把手放在我的腰上,害怕他的肌肤贴紧我的肌肤,害怕他哪怕蜻蜓点水的亲吻--是谁说过?女人可以跟她不爱的男人做爱,却不愿意和她不爱的男人接吻。
他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他是我的丈夫。可回应的是这样冰冷麻木的身体,是一堆死灰,一截枯木,所有的欲望和激情都被埋葬,被压抑。身体是要跟着心一起走的,身体也和心一样无法控制。
是因为在心里念着另一个男人,还是因为不曾出世的孩子?是连我自己也把握不了的心思。
他比我更明了,指尖轻触时我的瑟缩,肌肤相接时我的僵硬,偏头避开他的唇,我最细微的动作都暴露着忍耐和厌倦。
终于,他第一次在夜间也提到那个名字,刺目的日光灯第一次亮起,他捏了我的下巴,逼视我:和他做爱你也像块冰?像个木头?
我甩开他的手,记不得多少次的重复:我从未和他有过!
他冷笑:我会信?
随你信不信。我冷冷地看他:你知道我怀孕了,我只是怕影响了孩子。
孩子?他把目光停留在我已经微微隆起的小腹:现在你心疼孩子了?去年你怎幺没心疼孩子?宫外孕是不假,可是得多剧烈的床上运动才能导致大出血呀!
我无法呼吸,无法言语,浑身发起抖来,整个人哆嗦的像一片风中的树叶。他一把扯过我的头发,逼近我的,渐渐扭曲的脸:这是我的孩子吗?我的孩子值得你这幺爱惜?只怕是你喜欢的那个男人的吧,孩子生下来,是准备让他姓沉,还是跟着养父姓廖?
我眼中已经无泪。胸中却燃烧起一团熊熊的,决然的火。
玉已碎。瓦亦不能保全。
第二天,我请假去了医院。
心甘情愿的放弃。我四个半月的孩子,用不了一个月就可以在我怀中蹬呀踢呀的小小生命。
冰冷的器械钝重地进入我的身体,极致的疼痛里,忽然有了如释重负的轻松,忽然又有了想要飞翔呐喊的心情。
母亲接我回家。我少女时代的房间里,她一边恶狠狠地骂我一边给我煲汤。我一边听一边微笑。
妈妈。我想离婚。那个自由任性的桃桃,那个神采飞扬的林寞,不愿意活在无休止无穷尽的彼此折磨里,不愿意背负着沉重的无法洗刷的罪名踽踽爬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