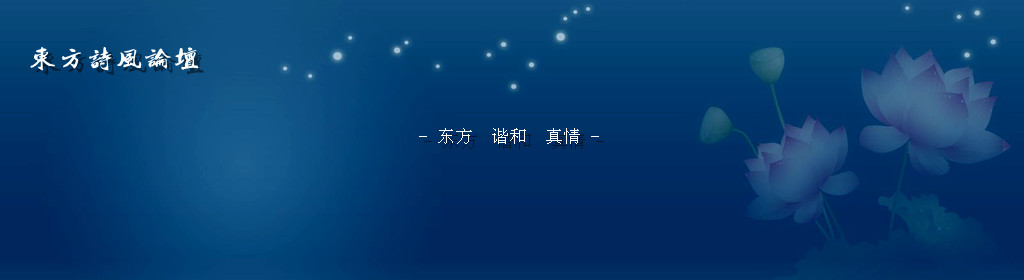晓曲兄在【奇異網文學社區】中的发言說:『谢谢游子先生转贴愚见,我于音乐没有过多的研究,于先生在东方诗风网的认识有同样的感受,即,“我觉得东方诗风诗友们提倡的格律新诗,那“格律”其实就是“音乐性”。不知道自己这个看法对不对,但是我非常希望我们能把这个“音乐性”真的与音乐连接起来,结合起来”。事实上孙逐明先生的格律理论就紧系这个内核的。所以于诗的发展方向问题,东方诗风和先生即这里的老师和朋友们有着很多相同或相近的看法,作为诗歌爱好者,因共同的爱好而融入其中,深感荣幸。』 晓曲兄:『那“格律”其实就是“音乐性”』這句話其實說得非常之對,雖然許多研究格律的詩論家,包括聞一多先生與啓功先生,未必認同這一說法。啓功先生在他的著作<詩文聲律論稿>開章明義就說:「本文所要探索的是古典詩、詞、曲、駢文、韻文、散文等文體中的聲調特別是律調的法則。但是,如果問這些規律是怎樣形成的,或者問古典詩文為甚麼有這樣的旋律,則還待於許多方面的幫助來進一步探索。」 我們不知道,啓功先生到底是不認同,還是真的不知道古典詩詞的聲律就是音樂的律,就是音樂性,它們是為吟、唱所須要;而吟、唱就是音樂。 但從音樂的角度看,『那“格律”其实就是“音乐性”』其實是千真萬確的。在朱光潛的【詩論】以及【文心雕龍】中的論述都證明如此。 關於詩與音樂的結合,我剛收到本網網友、法裔華人作曲家【詩期樂】先生的一封信,我把它貼在下面供大家参考: 游子兄:
或許您不知道,遠在十七年前,我曾認識一些中國留歐大學生,透過他們和大陸音樂人(當中還有一名還是我在歐洲認識的,經常同在一起用餐)聯繫,我努力遊說他們為詩譜曲(雖然我自己能作曲,但認為個人精力有限,最好群策群力),起初他們唯唯諾諾,後來不了了之,他們根本連一點熱情也沒有。 十七年前電腦剛面世不久,那時還沒有今天的網路連線,即使真的譜曲制成音樂,現在回想起來,真還不知如何讓音樂流傳(唱片公司肯定不會接受這種音樂作品的)。而今日,不但電腦功能比以前好千倍,音樂作品還可透過mp3網路流竄,這是一個大好時機,唯一仍不變的是,「音樂人」對詩的冷感依然如故。 事實上,許多知名的「音樂人」其實都是「經紀人」,他們 (上游音樂人) 承包一張唱片(稱為「音樂制作人」),然後發給每個「下游音樂人」負責一或兩首歌的編曲……。 再說,大部份「音樂人」「詩感」並不強,(今日所謂的「音樂人」普遍是指為流行歌詞譜曲的音樂家),您永遠無法指望他們因對詩感興趣而自動自發投身譜曲,近日我在「奇異網」讀到向明某篇文章,提及多年前台灣王永慶以高獎金「徵詩譜曲」事件,許多詩都被作曲家指為無法譜曲,就是最好明証。 看樣子要做到詩與音樂相結合,我們還有很多路要走。希望能與【东方詩風】的詩友們聯手興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