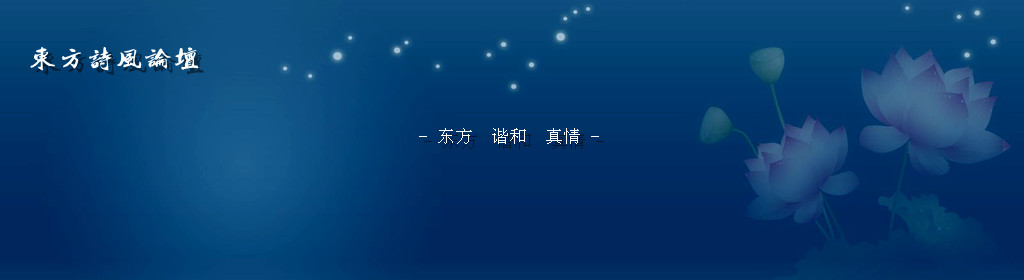以下是引用孙逐明在2006-1-5 19:29:56的发言:
是音乐的「律」,不是语言的「律」。
——这段话有语病。“音律”当然是语言本身的语音所具备的“律”,而决不是音乐曲调的“律”,只不过语言本身具备的“律”必须和音乐曲调的“律”基本吻合罢了。
把配合某个曲调的「音律」固定了下来,就是「格律」。
——这段话基本正确,但不够准确。准确的说法是:把歌词语音能和曲调配唱的普适性“规律”固定下来,就是“格律”。
同意。看来在这点上我们的看法很接近了。我曾经用「与音乐接轨」来想象你说的「和曲调配唱」,提法不同,意思接近。
我曾经打过一个这样的比方:如果音乐是一条轨道﹝一片原野﹞,中国的古诗歌就是借这条轨道﹝这片原野﹞去飞奔的列车﹝汽车、跑车、花车﹞;而这节列车﹝汽车、跑车、花车﹞能在音乐的轨道﹝原野﹞上奔跑,靠的是它的「车轮」–即「音律」或「格律」。
然而如此一来,我要提出提问的是:
一、 格律是应对某种特定的曲调而定的,例如七言诗与五言诗的格律不同;【满江红】与【虞美人】的格律不同,就是因为与之「配唱」的曲调不同而来的;这么一来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现代诗既然是一种不吟唱不需配曲更不需以配某种特定曲调的语言,我们怎样给它定「音律」与「格律」?
二、 语言的文学艺术有多种,例如散文是语言的艺术,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小说、说书、演讲、作报告等等,都是语言的艺术,然而它们都需要讲「音律」吗?我看它们都不需要「音律」,更不能为之定甚么「格律」。
说实话,以上问题我想了很久了,一直都对之觉得迷惑。因在此提出向孙兄暨诸诗友讨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