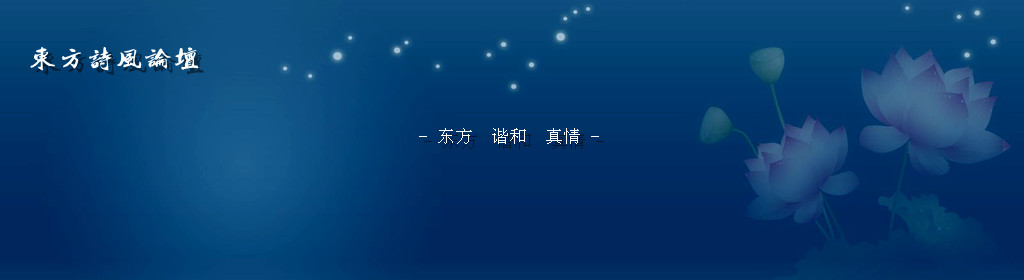以下是引用诗酒自娱在2006-1-12 9:12:53的发言:
现有的格律体新诗许多就可以谱曲,只不过作曲家视而不见罢了。
国外没有什么“歌词”,许多歌曲就用诗谱曲,有的优秀诗篇的谱曲频率极高。
相反,由于现在作曲技巧的高明,就是散文都可以谱曲的,例如红极一时的语录歌;现今的流行歌曲,有的其歌词也谈不上什么音乐性。
所以,我很同意“脱离歌唱的纯诗的音乐性研究的基础理论已经初步具备”的说法,以此知道格律体芯撒创作可也。
「现有的格律体新诗许多就可以谱曲,只不过作曲家视而不见罢了。」诗酒自娱说的很对。我对“格律体新诗”不甚了了,不过我相信,不但“格律体新诗”,很多有韵有节奏的新诗,都可以入乐。所以「现今的流行歌曲,有的其歌词也谈不上什么音乐性」,然而人们都能接受。那是因为现代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现在唱诗或唱歌,已经不必像古时那末讲究语言与曲调的配合,听者也能听懂,不会把不合音调的「你是灯塔」误为「你是等他」,把「难为情」听成「难为清」,等等。
不过你说「只不过作曲家视而不见罢了」,我对此话稍有保留。因为,那是因为长期以来诗歌与音乐脱离造成的结果。而这样的「脱离」,我们新诗界应付主要责任。是诗人而不是音乐家首先提倡这种脱离的。
我曾建议,我们设立一个「歌诗创作研究社」,就是意图让我们新诗诗人带个头,先建立一个与音乐界联系的「独木桥」,去促进将来可能出现的,像唐代,宋代那样,诗歌与音乐,诗人音乐家的紧密结合,以迎接中华诗歌另一个历史高峰的到来。
诗酒自娱兄,你多次呼吁「归来吧歌诗」,我很赞同;我以为,脱离音乐是新诗的最大损失。我还认为,理论研究是次要的,当前最要紧是实践和行动。
但是,我身处天涯海角,不知道那里去找认同我们的音乐界人士,因此也就不知道如何行动,从何做起。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