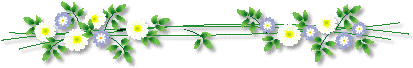Part 3 半阕红尘半阕歌(略)
对子质量已无求,能够得到美的感染、对得开心就足够了。
Part4纪念散文(1)
04年3月到05年上半年,是我笔头最勤的阶段,我的大多数散文,就在那段时间完成。怀念那些似水年华,快乐、心无旁骛地涂鸦。
杂思
今天囫囵吞枣浏览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蛮多感触的。
下午上网。又陷在音乐里忘我。疯狂地灌水,只为音乐。脑子怪怪的。我想到了很多,比如流逝的韶华,比如被沉闷压得快要折断的腰,比如猥琐的躯干充斥的罐装社会,比如一些闪烁的光怪陆离的念头,比如庄子鼓盆而歌送别亲人的洒脱,比如小刚的那首《台北的寂寞》,比如报纸上看似充盈着机智的语言泡沫,比如荷兰三剑客的空前绝后,比如刘欢蛰伏的耐性,比如公仆们嘴里时刻吐着的三个代表的象牙,比如马加爵事件离奇中折射的真实,比如中国足球自闭在了一个叫做草莽时代的箱子里面,比如台湾政客的道貌岸然,比如文坛的聒噪,比如风月社会的电台里泛滥的情歌,比如大面积存在的隐型失业在阴郁的天空撕裂的那道口子,比如……
总之,这是一个很俗的社会。想到了李熬的《斗士与镣铐》。作秀的成分居多。想到了王小波的那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有点灵魂归窍的感觉。人走了,他的思想还在大地逡巡。遍布暗礁的时代,风雨如晦,顾准却用自己的生命燃烧了一面小小的旗帜。“虽千万人,吾往矣”。他们的精神谱系呢?还在续写么?
想到了余杰,一个被冠为“北大第二个王小波”的才子。细读他的文章,哪里经得起推敲,遑论岁月的打磨。媒体,除了履行喉舌功能外,他们还学会了口若悬河——我切实领教了天花乱坠的意义。邵飘萍的身影已经渐行渐远。
很少看央视新闻联播,规范掩盖了陈旧,制度钳制了敏锐。每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已经沦为鸡肋。可怜的倪萍一脸认真的煽情,她自己居然毫无警觉。这是一个断层的时代,镶着金边的物事已经朽腐,嗷嗷待哺的人群却找不到依附,思想的,体制的,文学的……
社会在实质性上“亏欠”了我们,却用万花筒般的多样性做出了补偿。可以蹦的,可以买醉,可以觅春,可以豪赌,可以趁虚而入、各逞机巧掘自己的金子……整体在癫狂着狂欢,狂欢着癫狂。
我怀念一个摆渡的灵魂。人民用诗歌的海洋祭奠这位总理,这在世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将自己樱花般美好的生命牺牲,他把坚硬的纤绳勒肩胛。新旧两个中国,他和很多人一道,摆渡了一个民族。晚年,他老牛深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为了扶正一个民族的踉跄,他倒下了。夕阳滴着血。他走得太不甘心。
与之相对,舆论更习惯于用出发点去衡量一些功过参半的政治人物。唐吉诃德用尽浑身解数与风车鏖战,据说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
尼彩说,上帝死了。上帝是死了,但他的阴影还会长期罩在前方的路上。期待超人和更趋健康的群体。思想即使是在岩石上也会生根!俄罗斯民族近代历史上大批思想和文学巨匠最终提升了国民品格,即是佐证。
竖起耳朵。
=======================
荒漠腹内,还有月狼
让大地激情的颤动与痛苦的凝重导入筋络,汇合于你的颤动和凝重。
有一种动物,喜欢离群索居。所以,大漠深处,还有月狼,不一样的狼。
——它们很难构成群落,却能嗅到彼此的存在,于是暗中较着劲,在风沙肆虐中苟延残喘。生命,已被现实拉成一张弓了。森森的冷牙咀嚼着自己才懂的有关高贵与执拗的记忆。
——题记
一、破晓前的风
四月二十二日凌晨,大风让我不得安宁。
我住在七楼,风所眷顾的七楼。这里,它不知疲倦地重复着呼啸山庄的凛冽。整栋楼在惊涛骇浪中战战兢兢,象一叶扁舟。天还早,属于夜的静谧却被撕得粉碎。黎明还没有探头,它被吓傻了。
这样的风在大漠应该是司空见惯吧。我想起了只影走向大漠深处的月狼。
一年只刮两次风,横穿春夏与秋冬。风是大漠里流动的海洋,风之神在这个特殊的地域君临一切。他的威仪不容摇撼,他的权威不容挑战。梦里,大漠起风了。月亮惨无人色,哐啷作响。这位受自然之力加冕的国王哪里满足,他要把天地间的帷幕撕成千万条横幅!风象闪电那样急插而上,它又攀上了另一个音阶。大地在飘摇。只有目中无天的月狼,咬着冷冷的牙,睥睨冷笑,冷冷的目光如寒铁,捣向风云汹涌的长空。
耳贴着地,鼻尖上还有血腥的气息,月狼的尾巴卷成一个问号,爪子再也按捺不住了,它一头撞向风的铜墙铁壁,爪子渗出血丝。月狼的灰毛已经大块地脱落了很多,然而嶙峋的瘦骨并不能结成墓的形状,框住一颗狼心。直面风,它“只有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不为别的——只为梦中的美丽草原”;长啸冷峻而炙热,月狼潸然泪下。
昔日的山林豪杰狗熊在笼子里养尊处优,它用一个个认真到了极致、也笨拙到了极致的鞠躬换来了游人的厚赐:磕剩的瓜子,尽管这些瓜子可能是甘美的糖果,香脆的鱼翅和油炸排骨。它的卧室有灯具,月狼的有满天星斗;它所在的公园没有天井,月狼的领地却有旷野逶迤起伏。熊歆享着温暖,通行证是把身体整个交付给链条。
“……他们走着,走着,看到了花朵,脚步就慢了下来。”
月狼在这苦寒的荒漠,闭上眼,它看到了花朵,幻想着自己躺在一个升起袅娜琴音的摇篮里。那是月亮的白玉盘呵!这样,它的思绪可以海阔天空,飘忽不定。夜伏昼出,月狼做着自己的主。
栓住它心的,只有皎洁的浩月。
二、生存危机
北美育河流域,马修连恩《狼》专辑取材的地方。晨曦初露。瑰丽的梦被呼啸的子弹洞穿——为了保护另一种珍贵物种,狼被猎杀的命运似乎有点理所当然。没有畏惧,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只有不解在它们脑中盘旋。狼不屑逃走。仓皇是条射线,一旦开始就没有尽头。死亡或侥幸苟延残喘下来,都是高贵的注脚。生命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在荒漠发芽,开花,结实后,大地——绝对精神化的母亲会继续收容你们的,苦难的孩子。森森的牙,累累的骨,还会在月华初上的静夜歌唱,唱响静穆的月夜。
你们,又反击着什么?
三、早夭的狼
一片青春的白桦林,生机蓬勃。
可属于它们生命的灼灼其华,仅有一瞬。还有一种冰雪,可以一夜间把嘎吱苦嚎的它们摧残怠尽。
遇罗克、张志新他们的命运,白桦的命运。
太阳下山。收回一只黑色的风筝,磷光鬼火窜上屋脊。他们是被走火入魔的时代嚼碎的竹笋。破土的艰辛,未能出土的愿望,拔节刺云天的志向……
一群早夭的狼,只留给世界一块掷地有声的傲骨。
在茕茕孑立上路时,他们不经意间发觉了前簇后拥的蝴蝶,狼们热泪盈眶。幽深的诗意拔得百玉盘叮当作响,于是,早夭的狼行在了荒漠腹内,在远离中心的边缘,把大地激情的颤动与痛苦的凝重导入筋络,汇合。早夭的狼,还有孤月相伴,还有蝶舞相随。依稀一顾,红日沾在了荒漠脸上。
而与他们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委琐的灵魂,死后注定得不到救赎。
四、大雁与青蛙
读一篇散文诗时,我拾起了这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童话,轻轻插拭。直接引用如下:
两只大雁就要远行了,它们用一根树枝携带青蛙直上青云。乌鸦太太、啄木鸟大叔,还有狐狸大婶,老山羊伯伯羡慕极了。它们异口同声地赞叹道,“好一个聪明的青蛙!”“哇……”青蛙兴高采烈地应和着,它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竟忘记嘴里维系自己生命的小树枝。顷刻之间,从高天跌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我想起了那十年,用荒唐孵就的十年。
时代的魔手摇身一变,成了两只大雁。它们把青蛙送上云霄。树枝则是则是举国群众业已癫狂的心态。即使青蛙没有发出那句应和,小枝桠还是会折断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也象作者一样,笑不出来了。原因不太一样,我胡思乱想到了这些。
五、站在边上的勇气
钱钟书的皇皇巨著《管锥编》在险恶的冬天完成。这可能是学术史的孤例。熟悉成书环境的人可能会赞同这种提法。
批斗风潮里,钱老“有恃于内”,郎笑不改,阔步如昔。
如悬崖壁立,他在骇浪的撞击下泰然自若。柯灵先生对钱老的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在浮躁的类似“布郎运动”境遇中深思默存,这或许就是生存的智慧吧。拒绝中伤他人以自保,拒绝名利空棺的诱惑,甚至拒绝参加国宴。从“文化昆仑”身上,我窥见了一些月狼的智慧。站在人生边上,钱老用冷峻的眼神打量着大悲大喜。而另一位老人,在平凡昭雪的那一刻,竟是出奇的冷静。他身边的人都做不到,但他做到了。他的名字叫马寅初(因人口理论获罪)。
生命,已经被现实拉成一张弓了。
荒漠之内,还有月狼。
我也得谨慎。虽然吾之效狼,可能皆在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日远。但起码我得尝试一下。
=======================
童年模煳了
一
近些天,我总有耳福听到一首老歌——《妈妈的吻》,就是歌词从“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开始的那首。看到一把推开书本发愣嗅音乐的声源时,身边总有朋友在迅速交换眼神,然后发出有约而同的笑,“都这么老的歌,还听。”他们生拉硬扯,把我拽到球场或超市,好象那里才是安全地带一样。不忍拂大家的雅致,我只有可怜巴巴地让那熟悉的旋律一点一点消失。我觉察得到,它是不想从我耳边抽身的。人选择歌,歌也选择人。它们只对长着耳朵的心灵倾诉。
前不久自己也听过一首费翔的《故乡的云》。它也是老歌。只可惜我的故乡是个偏僻的山沟,幼时我只在长我五六岁的哥哥的小簿子上看到过它。哥哥还在旁边画满了一大堆再我看来倒更象跳舞的蚯蚓的云朵。那时,大人们劳作之余嘴里丢出的是调子跑得老远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一类的歌曲。另外,有关毛主席的歌总是难能可贵地从乡亲们口中唱出。几乎不识字的乡亲甚至不会唱错一个字。结果是他们总把歌声连同毛主席挂在锄头上晃悠,面有得色。还好,院里的哥哥姐姐都喜欢唱《妈妈的吻》之类的歌。那时的歌很抒情,唱着容易上瘾;现在的歌讲究宣泄,宣来泄去的负面情绪还是朝夕把人们缠绕。而我,就是父辈和兄长的老歌中觉得炊烟开始袅娜,小溪开始悠长的。我就这样懵懵懂懂接触了抒情。《故乡的云》里有这么一句: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妈妈的吻》牵着我回家,回到童年。自己带给童年和故乡的也只是一个空空的行囊。我还不会耍世故,可童年的一切都已经模糊。我身上几乎看不到它的影子。我还是学到了一点,那就是把新增的“见识”当作成长。
当我不满意自己写的文字时,有位朋友也这样安慰我:与他们(一个比较专业的文学论坛上的驻站作家)相比,我所欠的是经历,没准……于是“见识”某种程度上的代名词——经历,又出现了。我看到了自己的鄙吝,不想已经严重变形的生活再添这样一个借口。
童年,故乡,我回来了。通过《妈妈的吻》和《故乡的云》辛辛苦苦凿出的时间隧道。模糊的童年不成样了,上面结满了灰尘和蛛网。我是吓出汗来了!我特意拜访了幼儿园,试图以虔诚拾起几片儿时扮作敌人的玩伴“缴枪不杀”的清脆童音和一些眸子里的晶亮。
二
喜欢奶的我在十岁时还好意思向母亲提出这个要求。
据母亲回忆,我吃奶一直吃到两岁。无奈之下,家里把我送到了外婆那儿。可半年后我见到母亲,我奶声奶气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我还想吃奶!”连舅舅给我制的让我耀武扬威的玩具也受到冷落。母亲的乳汁,第一次让我知道了甘甜的味道。现在我想郑重加一句,母亲的乳汁是世界上最甘美的。
后来,我有了一个可爱的妹妹。那时,大伙已经开始滚锃亮的铁环了。清晨随着仓皇的鸡叫声一起热闹,唧唧喳喳的鸟韵也更浓了。我不久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比大家少滚的一天,在当时看来,就如同一年。我滚着铁环疯狂地上坡下沟,家里养的那条狗也跟在我屁股后逍遥。怕我与妹妹争奶,母亲也就懒得管我了。可惜的是,和我一样赤着脚追着铁环在秋天的田野上飞驰的狗却没有一个自己的名字。我现在还想念他应我的呼唤象箭一般窜过来把双脚搭在我胸膛或肩膀的情态。听着他鼻子里哼出的兴奋,我也就坦然接受了。
小时候我玩得很疯。当父亲抽出一根稻草作势要打我时,我总是这样央求,“爸爸,等我长大打了就不会这样了。要不了多久的。”——即使被大人用稻草责打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啊。那时我们都可怜蝉,老是抱怨酷暑怎么还不消去,害得它们一声接一声地痛苦长叫。而我们自己,盼望长大的脖子伸得比鹅还长。
上学前,我居然学会唱《妈妈的吻》。它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支歌。处在川东北的小山村,乡亲们不知道普通话是何等怪兽,我自然也就丝毫不懂这首歌唱的到底是什么。这支我学舌唱会的歌甚至让在小学念书的哥哥姐姐惊奇不已,双手按住我的脑袋端详了许久。“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等我可以“字正腔圆”地唱它时,小学已经在向我招手了。上学后,我也并没有乖起来。我把捉来的小蛇搁在讲台女老师的粉笔盒里,结果她竟然威严失尽,尖叫了一声,急速后退,头结实地碰着了后面的黑板。
纳凉的夜晚,我爱扛一把竹椅,坐到院子听大人讲那神奇的故事,但总是托着腮睡着。母亲抱我回屋子时,我又总能够出乎意料地醒来并吵着要返回院落。母亲只好等我睡着后,和父亲交替为我摇着竹扇。
稍大些时,我学会了烧饭。抵挡不住自告奋勇的我的软磨硬泡,母亲不放心地答应让我为全家做早饭。事毕,我总是得意地把父亲喊醒,象胀红了脸才生下一枚蛋的母鸡一样骄傲。经常在外的父亲强压着倦意听我卖瓜。
也正是再那些早晨,我听到了仿佛近在咫尺的汽笛声。是那么近。听说,山外的世界很美丽,我也就开始象点样子地用功了。我缠着父母要来零花钱,买了不少作文书(那时唯一的课外读物或曰参考书)囤积居奇。——当时,自己的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体同学面前朗读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
夏天的傍晚,我爱到山梁那边的小水库的堤坝上玩。离坝约两米多的地方有一个石头砌成的“龙眼”(下部有孔,穿过坝子作排水之用,平时是塞上的。系方言)。不少高我一头的大孩子便跳到上面,雄赳赳地站上一会,便跳会坝上,收获我们惊慕的眼神。我却不乐意这样了。一个下午,顶着他们比狂风还厉害的怀疑目光,我暗忖了好一阵,最终决定一试!哪知我用力太猛,结果过犹不及,落在了“龙眼”前方的水中。听说,大伙全都傻了眼,任不会游泳的我挣扎三次后沉入水底。正在拾柴的母亲知道后,却一下子坐在地上,怎么都起不来了。第二天凌晨五点,在水里淹了一刻钟左右的我苏醒过来。夜里,我家围了几十位不肯散去的乡亲。据说,我被捞上岸时,已经间歇性停止心跳。多亏了邻里,我才能重新贪婪地呼吸空气、享受阳光。他们有的喊医生,有的牵来水牛,说牛背的热量多,便把冰冷的我扶在水牛背上。有的长辈摸了我的胸口,见还有一丝暖气,就根据民间的说法捂住了我的肛门,把我头朝下倒出咽下的水……
三
这些,都宛在昨天。怀念童年,感谢生命的际遇,感谢乡亲,感谢我的父母。
童年越来越模糊了,我,泊在了童年和世故之间的泥土上。
=======================
故乡
1.
我立在万物冻结的异乡街头。寒浸泡着身体,吐吐舌头,我折向一座荒凉透顶的崇丘。那儿,有挽住白日余温的月光。
夜,恬淡如菊。
夜色很美。齐膝的草枯黄,涌动的暗香让眼睛锃亮。山林四季都有一种味道,让停留的脚步一寸寸悄悄陷入,舍不得离开——我谓之为香。山像月球表面一样荒凉。有的只是密布沟痕的石头、枯草、丛林和一些龟裂成各种痛苦形状的土地。这让我想到了男人的形状——他的沟痕,他脚下丈量过的丛林、枯草,他龟裂的爱情与曾经的诗意想象。尽管如此,它还是捧出一种香,在薄雾和月色的毛孔之间徐徐挪动、铺展。想到月,我温暖了些,想起了夏日不堪酷热也是掉着舌头的狗,不由放肆笑了。它没能持续多久,我那对冷空气极敏感的鼻子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这里,一样苦寒,不因朗照而显得和颜悦色一点。泪出来了,当然只能是鼻子的痛扯出的。
我并不是无家可归才来这儿,但情形也大抵相似。“所谓故乡,不过是我们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一站”;所谓故乡,不过是给摇摆后恢复平静的心灵提供短暂休憩的摇篮。我喜欢这儿,原始的野和躁动在冷风里张牙舞爪。耳朵仿佛听到了蓝色磷火在噼啪作响,和火苗吻过竹节的声音一样。与其默守一生,不如委身给痛快的燃烧。
我是山村的孩子。这些年来,一直忙于缝补差距,一种自己与社会对一个普通人的要求之间的距离,一种对我心智的勒索。我还不会耍世故,可童年已经整片模糊。月色变白了。风从后脑勺轻轻擦过,猛地攀上几个音阶远遁。连尾都抓不到。一块木头断为两截,彼此分离;一年被分为春夏、秋冬两瓣,彼此分野;人生锯成两段,彼此隔阂:
2.
儿时,我们滚着油亮的铁环把清晨闹醒——不彻底不罢休。公鸡母鸡全都仓皇而逃,正做妈妈的母鸡也拖着拙笨的步子惟恐落后,鸣啭的鸟韵更浓了,只有家里威武如军犬的狗紧跟我追着铁环领略在田野阡陌翻山下沟的恣意。有时,它会把铁环、我甩得老远。但没多久,它就会洞悉这一切,箭一般折回,把双腿搭在我肩上,鼻子里兴奋、得意暴露无遗,“哥们,耍我啊?”而今,“蓄意多拆线”,叠床架屋的准则已经把童年的衣服破坏得惨不仁睹。两段人生彼此隔阂。
童年的轻舟过了十重山,就不再轻盈,不再属于童年。
“雾失楼台,月迷津度”,一切都显得飘忽、不肯实在。某种程度上,人成了一个粽子,内部填塞了自己并不乐意的东西,然后喂给一台总是饿着的庞大机器,剩下一张掏空了的皮。
记得阿基米德临死时带着商量的口吻,“不要弄坏我画的圆圈?”这彰显了双重意义:1)他还有一个为之嵌入生命的圆圈。我所能做的,惟顶礼而已。2)圆圈在生命终结的刹那遭毁,何其可悲。但它无碍于阿基米德的伟大,显然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哀。悲剧在于,世俗的力量在蛮横吞没一具生命时,还追加了对“圆圈”的鄙夷和嘲弄。
月光盈怀。月光,与世间的真情并蒂,安抚我们这些孩儿,使我们不至于完全断乳、苟安于卵翼下。“假如一个人放弃了真理,他必定是出于某种形式的恐惧”,这是甘地《消极抵抗》中的话。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的圆,只是很少有人懂得消极抵抗的积极意义和高尚之处。可惜,他最终没有产生象泰戈尔在《文明的危机》中那种对英国文明侵略性的清醒认识。
清醒的本质都是相似的。在这一座荒山,在这个扑朔迷离的夜,我愿意重读《文明的危机》。捞回我的圆,我的故乡。
诗意是失散在齐腰荒草的一粒嫩芽,我愿意向她投去脉脉的关注。我看见了山下人家的灯火,象披上了一件穿了几水的旧衣。
“人”,还可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回到故乡。
=======================
征文而作
我是湖大的一名学子,一名而已。下面的文字,也只是我一个人的比划。
在这个唯效率是瞻的时代,语言大多是以泡沫的形式出现。推多了,敲多了,多累啊!累己是个人私事,但累人就截然不同了——那是不厚道的,是对人家本体生命的蚕噬、凿打。“厚道”随《手机》摇身一变,一度成为最流行的词语之一,鹤立于时髦词汇T型台的前方。因此,语言沦为了一种不能触及隐痛的抚慰,一种礼貌性的空洞赞美,一种蜻蜓点水式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点的重叠,一种刹车失灵后轻松情感的率性爆发。
报刊上不乏这种词汇,口头交际中它更是时常派上用场。
个人比较反感这些泡沫。乍听之下,还以为是一株迎风摇曳的树发出的悦耳声音。细辨之,原来这家伙周身挂满了噱头一样的铃铛。悦耳也就止于悦耳,难以怡情。所以我不愿意把现成的几个花环稍作翻新,献给我的湖大——一个前身经历了历史风云际会后蹲在现实边缘的落魄贵族。把“千年学府”、“潇湘洙泗”之类的词眼“献”给他,可能跟扔他几颗磕后的瓜子一般,会让他抽搐、气结。现代学子怎么就会这一手呢?
我们勿庸为贤者讳。今天湖大的情形很难一言敝之。我想借朋友的一首诗来表达(换了几个代词):
活在纸的背面
他在纸的背面
坚韧地活着
他被涂满各种颜色
甚至被四分五裂
然后丢弃到被遗忘的角落
此时他更需要
一个可以尖叫的喉咙
湖大在学术界、思想界的影响远不如其前身岳麓书院。历史上尽管这里鲜有状元产生,但大批经世致用之材正是从这个小小的庭院带着躁动“狞厉”的风吞吐而出。余秋雨的《千年庭院》已有名单记录,我不想再作赘述。
“合安利勉而为学,通天地人之称才”,他拥抱的是一种卓尔不群的自信和气度。其实除了这些史载的名字,书院在一条罕有人迹的隧道独行的力量还来自于众多耐得住寂寞的灵魂。枕石客、挂瓢人抛开名利空棺,埋首山间孜孜打磨识见、品性;告别书院后,他们或执教乡野,或在市廛敛神倾心著述,或为官一方勾勒一片隽秀的土地……而遭逢社稷动荡时,他们又总会现身。船山先生在湘西瑶洞如豆的灯光下与光阴赛跑,灵台擎着“六经责我开生面”的使命;元初的学生,更是血洒战地黄花。
爱尔兰人萧伯纳对爱尔兰人的生活态度这样描述: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块土,一只猪……撕下了面子,血淋淋的,怪可怕,怪难为情。这偏偏象极了我们民族的写真,我不得不说。还好,只躲在文字里咕哝两句不至于犯了众怒。我个人看来,这些书院的俊才也很少有例外——宇宙广阔,时空无涯,社会生活“汪汪如万顷之陂”,而他们却都象工匠沉湎于手艺一样结蚕侍弄自己的那一块园子。敝帚自珍可以理解,但园子只能在园子的意义上作有限度地延伸。
时光在现代勒马。这是一个唯效率、唯财富是瞻的社会。这个遗憾已经不存在了——不是从我们无法感知这个角度上得出的,而是我们在挤乘物质快车的时候丢失了自己的“圆圈”。阿基米德的生命有些逼仄,他本可以甩开并超越那一大串“**家”的头衔,构建出社会意义、公众意义上的一种自我精神的应和;但有一个让自己嵌入生命的圆并差点蔚成方圆,他无疑是伟大,足以让作为现代公民的人们蒙羞。
想到了RobertFrost的《TheRoadNotTaken》。我殷切地期盼我的湖大,我们的湖大会坦然掘着一个不一样的山洞,继续传递、拓宽悠悠千年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