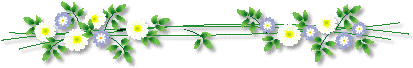□本报记者 杨子 ●食指,原名郭路生,著名诗人,被称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小学开始热爱诗歌,20岁时写的名作《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阿城插队内蒙古时托人抄录了食指的全部诗作;陈凯歌考电影学院时曾朗诵食指的《写在朋友结婚的时候》。1973年食指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入北医三院就医。出院后继续写作。1990年至今在北京第三福利院接受治疗。2001年4月28日与已故诗人海子共同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著有诗集《相信未来》、《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诗探索金库肥持妇怼贰ⅰ妒持傅氖贰?/p>
出租车在烈日暴晒的京昌高速公路上开了好大一会儿,才来到昌平县沙河镇。路边看不到第三福利院的标志牌。沿着一条狭窄的危桥走进去(桥下是一条污染得漆黑的河,河边是因污染而分外茂盛的青草),不远处,一道围墙围住的地方,就是第三福利院了。病房掩映在绿树之中。走了好一会儿都没见到一个人。一只大鸟在很近的空中叫,既不悲伤也不快活。很快,在树木后边看到了晃动的身影,是一些女病人在悄无声息地晾晒衣服。
食指(郭路生)所在的第二病区是一幢小楼的第二层。走廊尽头的那间屋子是他们看电视和聊天的地方。当我们出现的时候,一屋子的人好像谁都知道我们是来找郭路生的。但他们可能谁也不知道这个和他们朝夕相处、为大家擦了七年楼道、洗了七年碗、和他们一样是疯子的病友是个大诗人,在成名三十多年后,刚刚获得了人民文学的诗歌大奖。
食指从那一堆浅蓝色条纹病号服中出来了。一个年轻的大夫给我们找了一间办公室。
刚一坐下,食指就很突兀地说:“我想谈谈时尚的问题。我觉得时尚的问题一定要引起注意。这牵涉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时尚是短期的,泡沫的,是带有商业色彩的一种表面的东西,不是内在的。”
“你对这次获奖怎么看?”
“我觉得这奖主要是鼓励一种文人精神,也就是不讲时尚,纯朴一点,朴实一点,不要让人感觉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社会上应该保持一个正确的导向。奖励我主要是奖励一种文人精神,就是这些年来真正能坐冷板凳,真正静下心来在那儿写作,不浮躁,不为名利。真正的,不是假的,装门面的。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我时,我说不希望炒作。有时候一些奖励和报道会把我给弄得很乱,不会像以前那么能静下心来。”
“社会上怎么议论你,你知道吗?”
“我把自己定位为疯子。我戴着一顶疯子的帽子,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可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爱怎么想怎么想,因为我是疯子。”
食指在一根烟抽到头的时候续上另一根烟,说话有点漏风,上边的一排牙已经没了一多半。“我的牙给医生看坏了,他给我钻劈了。” 少年天才
记:你最初是怎么爱上诗歌的?
郭:那是在小学。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抑扬顿挫和押韵。小时候,别的孩子都在看《三国演义》的连环画,看苏联反特小说,我已经在看诗了,比如《给孩子们写的诗》,我能感觉到那种美。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也看不懂,还大段地抄袭,然后投稿。
记:你母亲对你也有一些影响吧。
郭:对。我妈妈给我读的诗很浅显,“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一读就懂。我觉得非常奇怪:怎么那么好?这种语言非常神奇。那是小学四五年级的事情。诗的美不是一般的。
记:你最早开始写诗是什么时候?
郭:小学四五年级。那时写打油诗,“鸟儿落在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老师阿姨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好。”就这样写着玩。
记:最早被老师和周围人注意到你写得不错是什么时候?
郭:初中。那时一些同学就议论我,说这是个天才,都是女孩说的。
记:早年何其芳对你影响很大。
郭:对。我写这些诗的时候不知道诗的规律,我只知道诗歌是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何其芳知道我写诗,就跟我讲,诗啊,是有格律的。
记:你喜欢他的《预言》吗?
郭:非常喜欢,它非常精巧。何其芳是非常健谈的一个老头,他跟我谈得特别多的是马雅可夫斯基,他说那是大师。何其芳的《预言》显示了中国人心灵的那种精巧,感觉的细微。马雅可夫斯基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大气魄,粗野,有生命力。马雅可夫斯基比惠特曼要粗野多了。这就让我想到中国文人的生命力的问题。马雅可夫斯基有一种滔滔如江河的东西,而我们中国诗歌却像水乡一样。
记:我正要提到类似的问题。何其芳的诗歌有一种阴柔之美,比较唯美主义,你的诗歌很硬朗,很强大,在悲伤中透出一种力量,这和你的性格有关,还是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
郭:一方面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我疯了。我跟贺敬之也很熟,贺敬之说过,说小郭的诗有风格,说一读就知道是你的诗。我就琢磨,我喜欢什么样的诗?什么是我所追求的?我记得李大钊的一句话,“从凄凉中看到悲壮 ”,我最喜欢这个。我有这样的诗句,“身世如秋雨般凄凉,内心却落日般悲壮。”我追求这样的境界。
记:《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整个六十年代最震撼人心的作品。请谈谈当时的创作过程。 郭:送别人走的时候我也写诗,写完后就觉得不是自己要走的那种感觉。到我自己走的时候,我又写了一首,是在火车上写的。火车开动以后,跟一些朋友聊了聊天,到夜里我就找了一个很静的地方开始写诗。写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母亲缀衣扣的针线。我开始想了很多,写了很多。火车开动的时候不是有那么“咔嚓 ”一下吗?就是那一下,一下子把我抓住了。
记:有人说这之前你写的送别歌是歌颂上山下乡的?
郭:因为我觉得必须锻炼。我写的是,“响起来了,响起来了,响起来了,车站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因为这是鼓励一个初步的儿童迈开步伐,走向光辉壮丽的人生。”
记:当时那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对你是不是有决定性的影响?
郭:大开眼界。
记:这些黄皮书的诗人对你影响最大的是谁?
郭:叶甫图申科。他的《娘子谷》并没有给我很大的震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没意义的孩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在这残酷年代,我曾经歌颂过自由。人们说我多大胆,不是我大胆,在这严酷的年代,普普通通的诚实便被称为大胆。”语言漂亮极了。我跟朋友们说了,他们都去找这首诗,都说找不着。
记:你们那代人都经历了时代的疾风暴雨,大家都有很多苦难和挫折,这些最终是否都成为你诗歌的一种养分?诗歌对你来说是一种释放或者说治疗吗?
郭:痛苦对于诗人是一种财富。而诗歌是释放和治疗。我内心的痛苦变为诗了,我就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满足。诗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敏感,别人没有感觉到的地方,他敏感到了。一个景物,一件事物,在别人心里没有留下痕迹,在诗人那儿就有痕迹;第二点就是,痕迹积累多了,不把它表达出来,这个痕迹还积在我心里,非得把它写出来。
记:你第一次去见何其芳是什么样的情景?
郭:何京颉后来写文章说见我的那天何其芳特意换了衣裳,我不知道。有一天,何京颉说,去看看我爸爸。我说你爸爸是谁啊?她说我爸爸是何其芳。我一愣,因为中学课本里有他的诗。我就去了。那是夏天,我穿一条短裤,一件背心,像小孩一样。何京颉说我是写诗的。何其芳就请我喝红茶,叫他女儿多放点糖,说好喝。当时我还真不知道有红茶绿茶之分。何其芳是很温厚的一个老头。最让我吃惊的是他的字。字写得秀气极了!像女孩的字儿一样,又小又秀气。老头给我的《鱼儿三部曲》和《海洋三部曲》提过意见。一个很好的伯伯。没想到那么快就去世了。
记:在技巧上他对你帮助大吗?
郭:最大的帮助就是(教给了我)新格律诗,所以我后来写诗特别整齐。知青时代
记:戈小丽(翻译家戈宝权的女儿)说你在乡下给那些知青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时候,把他们念哭了。
郭:可能那时候没有反映那个时代的诗,并不是我的诗特别好,如果有个比较,我还不一定能成为佼佼者。没有人反映知识青年的心声。我是惟一写这些真实东西的人,所以他们印象特别深。这是特殊环境的产物。看了这本诗集(《食指的诗》)人们才知道,那个举着语录、喊着口号的不可思议的时代,还有那么多欢乐和苦恼,还有爱情。(多年以后)我的诗成了古董了,我对这一点很不满意。人们评价我的诗歌时,总说六十年代的那些,这么做我非常不满意。我疯了以后,七八十年代写的那些诗更有价值。
记:你把他们念哭了,这是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这是不是你对诗歌效果的一种追求?
郭:诗歌的力量就在于……当今这个社会,诗歌太不要脸了,诗歌已经太惨白了。
记:1969年,你在汾阳县杏花村挣了很多工分。山西农民好像很幽默,语言很生动,这种民间的东西对你的写作有没有帮助?
郭:我在下乡前就认识贺敬之了。我给他念了我的诗,他一愣。他说要放在三十年代,这是好诗。问我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我说准备下乡去,去山西。他说好啊,山西民歌多,让我多学民歌,可以让语言更明快一些。我还到何其芳那儿找了很多民歌,何其芳不喜欢民歌,都让我拿走,我背了这么一摞子民歌到农村去看。所以我后来在乡下写了一些民歌体的诗歌,比如《窗花》:“地主窗上冰花在/俺家糊纸花不开/红纸巧手细剪裁/一朵窗花剪下来//太阳一出乐开怀/温暖穷人心里揣/地主窗上冰花败/俺家窗花向阳开。”
记:你在农村的劳动对你后来的生活和写作是不是有很大影响?
郭:谢谢,我非常愿意谈这个问题。这让我终身受益。别人不理解。“伤痕文学”出现的时候,我就有意见。你才下去几年,才受那么点委屈,就在那儿喊,就有这样大的抱怨,这样大的不平。农民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是那样的环境,他们到哪儿去说这些话?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去改变农民的命运,改变农村的现实状况?因为农村的改变才真正是中国的改变。中国是个大农村,只有农村好了,城市才会好,国家才会形成良性循环。
记:“文革”开始以后,红卫兵运动很壮观,如火如荼的,但你的热情始终是在文学创作上。在《鱼儿三部曲》里,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你对当时的情势已经有了非常深的忧虑。当人们都在随波逐流的时候,你怎么能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郭:文革前我就挨整,我已经看到这代人的命运了。鱼儿跳出水面,落在冰块上,它的前途是死,和这个冰块一起消亡,但它却看不到冰块的消亡。后来我又写出了《相信未来》,相信我们会战胜死亡,这已经进了一步了。我年轻,我能看到冰块消亡的那一天。
记:插队的时候你的诗已经传遍了所有有知青的地方,这真是个奇迹。
郭:所以有人说我的诗歌的版本是最多的,抄出各种各样的来。当时人们觉得那个社会沉闷得不得了,但那时也还是有希望有欢乐,有忧愁有哀伤,有爱情,我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了。我现在想想,是这些打动了年轻人的心。为什么大家那么传抄我的东西,是因为那个时候社会上有些人朦朦胧胧有感觉,但不敢露出来。我把它写出来了。
记:江青是怎么看到《相信未来》的?
郭:这事我听好几个人说过。那是1969年,我下乡第二年回来,四三派的人回来聚会,要我去。我给他们背了几首诗。那些诗他们要走了一些,作为一个动态写进报告里,给了上边。有人说江青说,这是一个灰色的诗人。又有人说江青说“相信未来就是否定现在”。你不歌颂文化大革命,不相信现在相信未来,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记:我们能不能说从1969年到1978年的诗人郭路生是另一个郭路生?
郭:可以这样说。
记:这段时间你写了不少政治诗,尽管那些诗很形象,有特色,但它们总还是应景之作。
郭:我是要一辈子搞创作的,不发表东西怎么办?怎么活?明摆着的嘛!
记:就是说你还是需要社会的公开承认?
郭:对,对。咱们实话实说。贺敬之看到这些诗非常吃惊,专门找我,说写得不错。
记:实际上一些早年很优秀很有影响的诗人,包括何其芳、郭沫若在内,都写过这种应景之作,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而且你的那些诗中有纯真的激情。但你有没有想到它们在你的写作中也许是不那么重要的?
郭:不,不,很重要,那是我年轻时代的一种非常幼稚的、非常可爱的、想让社会承认的心情。比如《我们这一代》,我是很真诚地写的,“虽然还残留着/黑夜的痕迹/但黎明终归/还是黎明。”跟别人就是不一样,这还是我。“一轮火红的朝阳/突破了迷雾重重/升上了我们的双肩/那气势磅礴的山峰”,这还是我们这一代人啊。“我们健康,朴实,一身光明/就像早晨的露珠那样晶莹/但这绝不是一滴普通的露水/它用生命闪烁着太阳的光辉”,这不是很像我们这一代人吗?所以我并没有出我自己的那个格。我写这些怎么不正常了呢?在贺敬之表扬我之后,我去找了他,结果跟他吵起来了。
记:为什么?
郭:他让我学学政治,别那么歪,谈恋爱啊,喝酒啊,吸烟啊。在福利院
记:在福利院的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郭:苦,但是我学会了不发愁。在这里呆着使我健康,生活更实在,更扎实,更充满信心,更有力量,更有热情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这意思。“文革”那几年,我非常喜欢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我希望有更多有中国气派的作品出现。中国气派,我对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我就琢磨什么是中国气派。后来邓小平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就想到,只有中国特色,才有中国气派。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有一致的地方。我在这里考虑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要写文章。但这里条件太差。我得有一个创作的环境。
记:那你现在怎么写东西?
郭:这两年我就写了两首诗,苦死我了。(给我们念了一首2000年4月创作的《青春逝去不复返》。)
记:你们几个人住一间屋?
郭:5个人。十三四个平米。
记:你的病友知不知道你是诗人?
郭:知道。
记:他们搞活动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朗诵诗歌?
郭:会。
记:你说不能写诗,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是吧?
郭:没有一个环境。我不能在病区里写东西,得住在病区外边,因为我得熬夜写作,白天睡觉。我可以先买一些馒头花卷回来,睡醒了再吃。这儿(指病区)不行,吃完饭很快就得睡觉。我现在都是想起几个词儿,然后记到本子上。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个人独处的时间)。
记:不能到楼下,到外边的小花园里去写吗?
郭:下不去的。你出去了出事怎么办呢?
记:晒太阳怎么办呢?
郭:一大堆人一起去。
记:这些年都这样吗?
郭:十多年了。很多人不相信,说是神话,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能写诗。我是疯子,我在我自己的王国里是国王。很多东西,我放下了,我自在了。我不求酒色财气,我把这些放下了,我就自在了。
记:你在这儿应该算轻的病人。但他们中会有一些重一点的病人,你和他们怎么相处呢?
郭:有一个50多岁的老头,有一天我正在打水洗脸,他照着我的后脑勺给了我一棒子,“梆”的一声,棒子打折了一截。打了也就算了。后来这人自杀了。
记:你在农村插队时就非常吃苦耐劳,到了福利院也一直在擦洗楼道、洗盘子,这些活你做了多久?
郭:7年。每天擦两遍楼道,洗三次碗,以前没有消毒碗筷的时候一天洗六次碗。现在做不了了。(食指做过第二病区的区长)
记:是你自己要求做的吗?
郭:对。
记:那段时间写了不少东西?
郭:我写出了《人生舞台》等不少有价值的作品。
记:常回城里吗?
郭:几个月去一回。一般是夏天回去,冬天我回去过春节。
记:在这里平时有什么消遣呢?
郭:大家就是看电视。我不看,陪朋友聊天。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谈,有些看法水平很高,至少他们懂得老百姓的道理。
记:你在这里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郭:写出诗来。
记:你在这儿能听到贝多芬吗?
郭:听不到。公疗室有收音机,没有音响设备。那些歌,什么哥哥妹妹,谁听那个?贝多芬晚年的奏鸣曲很辉煌,很痛苦,也很超然。(前些年我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外国的音乐教授来讲学,为大使馆演奏,举办周末的小型音乐会,朋友通知我我就去。不要钱。那些大使和夫人们走进去,我就在边上呆着。我还托朋友带了两张贝多芬晚年的光盘,是100多号(作品编号)以后的。听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判断是对的。
记:哪天你痊愈了,回到北京的闹市中,肯定会有很多人包围着你,你怎么办?
郭:现在也是啊,老有朋友来看我,请我吃饭。我觉得挺好的,跟大伙儿聚会,给他们念念诗,挺好的。但我觉得北京不是家,回到这儿才是家,因为我把自己定位成疯子,回北京只不过是跟大家交流交流,听听社会上有什么事儿。
记:你每次回城里,都注意些什么?你觉得现在的北京和你少年时代的北京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郭:那时更有人情味。
记:如果你出院了,你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有什么要求?
郭:没有。只需要一个读书思考和写作的环境,只需要粗茶淡饭,没有过高的欲望。我觉得这里的粗茶淡饭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我没有高血脂、高血压这些富贵病。我的朋友刚跟我谈完,说你得改变改变环境啊。我也正愁着呢,怎么办呀,积累了那么多素材要写,又没有条件。前天民政部福利司的司长来了,他对我的诗也特感兴趣。我得静下心来,多熬夜,多读书,多写东西,多做点实事儿,因为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贴心地关切过我,所以我得用大量的精神成果来回报社会。
采访结束后,食指借了摄影师的手机给他父亲打电话。“6月20号接我回家,我得去镶牙。牙不行,吃东西老吃不饱。”
我们从医生那儿打条子把他“借”出去拍照。面对镜头他偶尔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容。他告诉记者,他想用自己的稿费租个房子,因为他要写作。他想冒这个险。
我们送他回到第二病区。他问了两遍:“没让你们白来吧?”
道别后,他飞快地钻进餐厅。开饭时间过去了那么久,一定是饿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