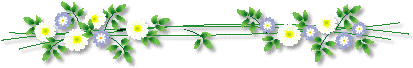|
《我的诗》里有什么
——读严希先生诗集《我的诗》
黄 皓 峰
总是觉得,诗人是一种了不起的群类。他们用一种充满感情的别样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剖析自己的灵魂。因此,在我眼中,诗人似乎总是带有一种独行于世的潇洒与孤寂:醒时,可目送归鸿,抚琴低吟;醉时,可仰天长啸,甚或末路一哭。纵常有穷年黎元之忧,却也不乏山水清音之唱。总之,诗人的生命是鲜活的。诗歌也应该如此吧。
我喜欢带着这样的偏见去读诗,读古人,也读今者。但当今的诗坛总是不乏一些自砸招牌的伪诗人、伪诗歌。任意的文字,随便的分行,晦涩的内容,杂乱的意象,以及故作高深的诗观,是他们自诩为“诗人”的资本,仅凭这些,他们便高昂着头颅向世人宣布:“我是诗人”了!当废话都可以入诗的时候,当不知所云的“深刻”成了好诗标准的时候,诗人还活着么?诗歌还活着么?
于是,便产生怀疑:今天的诗人究竟是“太有才”了,还是自己压根就不是读诗的料?现在,当人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是“诗人”时,真的还需要诗人么?还需要诗歌么?这种疑问一旦产生,便慢慢地对当代的诗歌丧失了兴趣——好吧,既然自己实在没有欣赏的水平,干脆就离它远点。所以,很极端的,在五六年里没有认真研读过一首当代人的诗歌。
直到读到严希先生的《我的诗》。
与先生只有过一面之缘,印象里残留的只是一位长者的剪影与他浑厚的嗓音。先生居然记得我,在他新的诗集《我的诗》出版后,还不忘托人给我这个后辈捎来一本。
一时惊讶!我真的不知道他还是一位诗人,并且早在十多年前就有诗集出版,并且——已经颇有名气!这在有些人恨不得把“诗人”的名号天天挂在嘴边的现在,显得有些“不正常”。自己也才真正意识到,已经许久没有读今人的诗了。于是,便去读吧。
素雅的白底上一枝傲立的腊梅,简简单单的题字——《我的诗》,没其它的了,封面一如先生最初的低调。我开始好奇,在这低调的素净之下,究竟会藏着什么?《我的诗》里,到底会有些什么?一页页地翻过,一遍遍地读过,我想,我找到了些许答案。
《我的诗》里,蕴藏着先生对诗歌的热爱。正如他在同名诗《我的诗》中写的那样——
我的诗/孕育在大地子宫/熔岩炽热/煤石沉重//我的诗/诞生在秋日黄昏/苍山韵远/残阳色浓//我的诗/行走在茫茫沙漠/孤烟无语/驼铃有声//我的诗/漂流在滚滚长河/惊涛拍岸/雪浪腾空……//我的诗/是大地的儿子呵/我的诗/是我不死的精神!
诗人一路走来,一路吟唱,从来没有放弃对诗歌的热爱。这种热爱,已经融入了诗人的生命,成为他“不死的精神”。只要这种热爱还在,只要这种精神尚存,诗人的诗情也终将会像炽热的熔岩般喷薄而出,化为诗章。并且,更为难得的是,诗人的诗歌写作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作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并不为逞才扬己而作,也不为出名求利而歌。他的歌吟,是出于“香草美人永在我心窝”的自觉,是“愿伴陶令醉唱田园歌”的期冀,是对“中华血脉绵绵五千年/没有诗歌就没有祖国”的清醒认识(《不要问我写诗为什么》)。在诗人看来,写诗就是自己的习惯,诗歌就是自己的必须,不需要矫情地为自己的写作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没有对诗歌真正的热爱,这份热情、这种精神,会是“不死”的么?
《我的诗》里,饱含着先生浓烈的亲情与友情。诗人早已脱离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懵懂,所以他的情感,有着一种经由岁月剥蚀、沉淀之后的平静与真切。在诗人的记忆中,对亲情的追述也许只能剩下一些片断,但将这些片断连缀起来,却有着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来看看诗人写他的母亲吧:
上午刚穿的新衣/下午就被树枝挂破了//妈妈坐在床边/一针一线静静地缝着//温柔的月光/在我佯睡得脸上徜徉//我那被不安挂破的心境/也被妈妈缝合了(《妈妈》)
摇篮摇醒月亮时/夜空的星星/纷纷来听妈妈的声音//顽皮藏进草垛时/袅袅的炊烟/总是缠着妈妈的声音//书包装满叮咛时/树上的小鸟/抢着模仿妈妈的声音//离愁叠进背包时/车后的烟尘/渐渐蒙住妈妈的声音//秋夜风吹落叶时/床头的台灯/无法点亮妈妈的声音//泪水濡湿睡梦时/浩茫的天地/到处都是妈妈的声音(《妈妈的声音》)
熟悉么?亲切么?诗人笔下的场景,只怕是你我童年时光中都曾经历过的吧!一幕幕看来,勾引起多少自己对往事的追忆。没有歇斯底里的嚣叫,也没有露骨的情感剖白,只是一点一点的,无意识似地将这份感情滴在了读者的记忆中,化在了读者的心怀里;不经意间,心已经被诗人的感情所浸润了……
对朋友呢?诗人没有刻意去展示自己对朋友的“义气”——这种表白多少会带有一些市井气——但可以看出,诗人对友情是十分珍视的。这种珍视可以融入对朋友的一声叹息的关切(《叹息》),可以体现在对陷入忧郁的诗友的劝慰(《伸出你的手掌》),可以寄托于具有侠肝义胆的朋友所赠送的老酒(《一瓶老酒》)。友谊没有必要时时都表现出一幅“两肋插刀”的模样,相反,君子之交淡如水,琐事之中见真情,危难时的关切固然厚重,点滴之间的关注会更让朋友感动,也更为不易。想必先生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吧!
诗人笔下除了亲情和友情,还有爱情,只是这份爱情已经化作了亲情的一部分。诗人已经过了在花前月下浅斟低吟的年岁了,浪漫的爱情誓词多少会显得不合时宜;况且,真正懂得爱情的人会知道,爱情到至浓时会转淡,当浓烈如酒般的爱情转变为一杯清茶时,才会更加让人口齿生香,沁人心脾。先生应该是懂得的。在他的抒写中,没有“山无棱,天地合”的激烈,也没有天荒地老的誓言。有的,只是无语相视时的一份恬静(《在海边》),以及与妻子分别时的不舍(《生命的航船》)。这已经化为亲情的爱,虽然没有了动听的誓言,却依然能让人感到一份“曾经沧海”的坚定与永远。
《我的诗》里,还有着先生的一份挣扎。这种挣扎,来自于对外界喧嚣浮华的反抗,也来自于对年岁渐长的无奈。美学家郭因先生说,诗人是“以一颗童心去面对世界”的,但成人对童心的葆有,却往往是对现实世界观照之后的无奈选择。这种观照世界的方式,给诗人带来了矛盾与困惑。因为在现实的世界中,是找不到童年时的那份纯净的。有的,只是物欲世界所带来的种种异化(《深秋的水草》、《列车上的印象》、《七月流火》、《蓝色玻璃窗》、《晚间街头散步偶得》、《无题》)。于是,诗人时常会觉得置身于一团迷雾之中——
跑不出去/跳不出去/游不出去/飞不出去//刀劈不出去/石砸不出去/火烧不出去/水溢不出去……(《雾中》)
这顽固而又混沌的家伙,使得诗人想逃逃不脱,想去寻梦却又无路可走(《在哪里》)。于是,诗人只能把企盼和希冀“虔诚地播撒在/黄土地宽厚的胸膛里”《雾野茫茫》)。由于岁月的剥蚀,诗人对生命的感伤、感悟以及壮志难酬的无奈,亦在诗里有所流露(《洁白与无奈》、《重生》、《无题》、《伫立原野》)。然而,诗人并没有消沉;为了保持心灵的纯洁和精神的不倒,为了获得滋养、慰藉和前行的力量,诗人不断地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妈妈》、《我的童年》、《夏恋》、《栀子花开》、《冬夜的怀想》、《往事如星》),通过对孩童纯真美善情怀的歌吟和对孩童时代生活体验的重温,来寻求现实生活中很难得到的纯洁、温馨和美好。
不仅如此,诗人的挣扎还表现在他总希望有一种力量能够打破这种混沌。这力量,有时来自于诗人内心的坚持——在时代的轻浮和躁动中,他竭力要看到“一张属于我的脸”;(《蓝色玻璃窗》)在世人的热情和热望逐渐被工业社会冷却的时候,他“猛地推开门/直冲到阳光下”,欲寻找未来的方向。(《七月流火》)有时,诗人也寄希望于外力,渴望鸟鸣如刃划破这团“浓雾”,以便摆脱这种窘境;(《雾中》)等待一个暴风雨的乐章“在雄狮般的钢琴家的指尖下崛起”,打破那令人窒息的沉寂。(《一个关于暴风雨的乐章》)当外力不能如诗人所愿时,他也想到了逃遁,想躲进笼着月光的梦里,以独善其身的方式,“享受虚幻和空濛”(《悲情》)。可是,在强大的现实面前,诗人真的能做到超然物外么?真的能寻到一方宁静纯洁之地么?对此,诗人似乎隐约有所透露,但又似乎什么也没说。而那只在《雾中》“划破了空虚”的飞鸟又是否真的存在呢?看看《一只麻雀》里的鸟儿吧,也许会有所领悟。
关于《我的诗》,还有很多内容未谈及。作为晚辈,我不敢妄称为先生的知音,只是凭着自己粗浅的识见说了一些并不高深的看法,相信其他的读者会有更为精辟的发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严希先生的诗歌是有生命的,不属于“伪诗歌”的一派,这话应该没错。相信先生今后还会有更好的诗作问世,因为——诗歌是他骨子里“不死的精神”。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13 1:57:49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