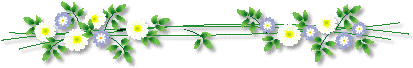格律化是新诗冲破困境并得以健康发展的通衢大道
引人共鸣和给人美感始终是艺术必须达到的终极目标,只不过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各有不同。 文学是通过语言来达到这个目标的,而不同的文学种类又有各自独具特色的达成手段。 诗歌,是利用富有音乐性的文学语言来塑造形象,向读者传递情感使之共鸣和创造审美使之愉悦的。因此,音乐性便是决定诗歌成败的关键。 白香山云:“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8)十分形象地说明了音乐性是诗达成其终极目标的根本保证这个真理:在肥沃的生活土壤中,诗人把情感的“种子”播下(根情);开始用形象的语言构思诗句,种子便萌芽了(苗言);而诗句自构思之始便是伴随着音韵节奏同时进行的,音韵节奏便是这株“树苗”开出的花朵(华声);只有经过了“开花”这个关键环节才能结出果实,这首诗才有实际的内容,它的存在才有意义,才可能最终达到感人娱人的目的(实义)。 因此,从诗人灵感的冲动(心中的诗)到作品的写成(纸上的诗)再到读者产生心灵共鸣并得到审美享受(读者心中的诗)的整个过程中,音乐性一直贯彻始终。诗,应该是“心灵纯化和韵律化情感的语言表现”(9),只有经过了“韵律化”的情感才能构成诗的感人肺腑的灵魂。 舍韵律而言诗,所言非诗。 否认音乐性而后言诗,实际上只不过是在“王顾左右”而已。 格律,是成熟的诗歌音乐性的根本保证。自南朝沈约发现四声之后,诗人们通过创作的实践和理论的总结,在唐初完成了格律体系的构建,从而为唐代及此后整个古典艺术时期诗歌的承传发展奠定了外在形式的基础;而中唐以后逐渐兴起的词和宋元以来出现的曲又加入了中国诗歌的行列,使汉语诗歌(就广义言,词曲也是诗的一种)的格律更为丰富。有了格律,中华诗词便得以叱咤风云、稳踞诗坛的主流地位千年而不倒。格律之功,不亦伟乎? 其实在沈约及其后的唐初沈佺期、宋之问之前,为确保诗歌的音乐性,不成文的“格律”始终存在。《诗经》的四言、《楚辞》的六言及乐府的五言,这难道不是一种“格”吗?至于压韵,则是有诗以来就有的一个“诗之为诗”的起码要求,是可以上溯到“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支古老的《弹歌》的。唐以后与格律诗词并行的古风,也并非是什么古代的“自由诗”。它虽不讲平仄、对仗和篇幅,可要讲韵脚;而五言、七言的标准字数、前者不能夹有杂言不能换韵而后者却可以、后者的换韵要平仄相间等规定难道又不是一种“格”吗?只不过比起律绝体严格的格律来,宽松得多罢了。新诗出现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作品均未尝废韵并保有一定的有别于散文的形式,虽无一定之“律”,但每一篇作品大都有着各自的“格”的“个案”存在,也并非是什么绝对“自由”的。你看,有诗以来,音乐性可是能须臾离得开的东西? 闻一多如下的话语很能发人深省:“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 (10)也是的,千百年来,那么多有才气的诗人何曾受到格律的丝毫“束缚”?他们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利器”为后代留下了感人肺腑的众多佳什! 作为诗,除了音韵节奏之外,还有它独特的语言叙述方式。徐志摩曾说:“音节的本身还得起源于真纯的诗感……一首诗的字句是本身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11)当这种“诗感”外化成为了诗的独特的语言,读者一看就可以知道这是诗,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诗语”吧。 “诗语”有别于“文语”,故有的所谓“自由”的作品,诗语的存在使它们保持了诗的身份。但是,“诗语”虽然弥补了格律的缺失,却不能完全取代它,“有句无章”从来就是诗之大忌。用零散的“诗语”堆砌的“七宝楼台”,是构不成诗的大厦的。新诗诞生以来被称为“自由诗”中的精品,除了使用“起源于真纯的诗感”的诗语外,都还需要保持着各自的“格”的“个案”存在因而不能完全“自由”,就是这个道理。 几十年新诗之失,就在于忽视了这个保证诗之为诗的格律的建立。文言时代过去了,白话写诗当然要抛弃旧格律而创立新格律。我们没有做到这点,而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做了却又被人为地长期搁置。这才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一条本不应存在的鸿沟,才使得世纪末的伪诗得以招摇过市。 我们浪费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中国新诗必须重新从文言诗语向白话诗语转型的衔接点(这种“衔接”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的第一天起就曾经开始过了)着手,继承汉语言的基本规律和借鉴诗词格律的的构建特征,在鲜活的时代语言的基础上去探索新诗外在形态的新的模式。 现在是以确立汉语诗歌新的格律为契机来保障其复兴、发展、繁荣,从而昂首阔步走向世界诗坛的时候了! 只有新型格律的确立,新诗才可能重新走上艺术的正轨,才可能重新引领中国诗歌新潮流,才可能成为真正具有“先锋”意义的主流诗体。果如此,则中国诗坛幸甚!吾侪诗迷幸甚! 中国的读者早就对“非诗化”的“诗”深恶痛绝到极点了!徐志摩尝云:“坏诗及各类不纯粹的艺术引起的止于好意的怜而笑,假诗(Fake Poetry)所引起的往往是极端的厌恶。”(12)“坏诗”仅只是指写得不好的诗,而“假诗”则根本就不是诗。人们期盼读到从传统文化继承中走来又沐浴着时代新风并能飞向世界的感人肺腑的真正而优秀的汉语诗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吕进先生提出“诗体重建”(13),并指出“‘破格’之后如何‘创格’”是“关涉到新诗的存与亡”(14)的问题,这对当前新诗的建设和发展,就具有十分重要和紧迫的意义。
中国的读者早就对“非诗化”的“诗”深恶痛绝到极点了!徐志摩尝云:“坏诗及各类不纯粹的艺术引起的止于好意的怜而笑,假诗(Fake Poetry)所引起的往往是极端的厌恶。”(12)“坏诗”仅只是指写得不好的诗,而“假诗”则根本就不是诗。人们期盼读到从传统文化继承中走来又沐浴着时代新风并能飞向世界的感人肺腑的真正而优秀的汉语诗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吕进先生提出“诗体重建”(13),并指出“‘破格’之后如何‘创格’”是“关涉到新诗的存与亡”(14)的问题,这对当前新诗的建设和发展,就具有十分重要和紧迫的意义。只有音韵节奏的全面回归,只有白话诗体的格律化,新诗才可能重现青春。 今后的现代汉语诗坛,应当没有“格律诗”和“自由诗”的区别,只有严谨的“格律体”与自主的“宽松体”的并存。有“体”才有诗,“自由”是无“体”的,因而对诗来说,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令人十分欣慰的是,近年间一股主张在诗坛拨乱反正、兴灭继绝的力量终于崛起了!从雅园诗派到东方诗风,这股力量在聚集,在行动!从实践到理论,一批格律体新诗理论家和诗人已经开始出现,一整套初具规模的新诗格律体系正在形成。近年来,他们通过艰巨的理论探索和勤奋的创作实践,取得了十分令人喜悦的成果:万龙生《格律体新诗论纲》、孙则鸣《汉语新诗格律概论》、程文《汉语新诗格律学》,都分别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格律体新诗理论;“东方诗风”网站论坛继去年编辑出版了《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中国文化出版社)之后,今年又联合世界汉诗学会共同出版了《2006格律体新诗选》(名家出版社),先后集中推出了刘年、宋煜姝、王世忠、余小曲、齐云、周拥军等十余位格律诗人的作品。而今春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王端诚的《秋琴集》,则是新世纪的第一部格律体新诗个人专集。 总之,当今中国诗坛,为扭转当前新诗面临的困境,为使新诗重新获得胜任“主流诗体”的能力,为保证真正具有先锋意义的汉语诗歌能在新世纪阔步前进,人们正在脚踏实地地开辟一条通往辉煌彼岸的大道通衢! 诗人们!不要太息“大雅久不作”,不要嗟叹“正声何微茫” !只要我们勤奋努力,不负时代所托,恢复诗之为诗的本来面目,就一定能够为汉语诗歌开创“垂辉映千春”的灿烂前景!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缪斯的信徒们,且拭目以待吧!
[注释] (1)《望舒诗论》,载1932年11月1日《现代》月刊。 (2)转引自苏汶《〈望舒草〉序》,上海复兴书局1932年出版。 (3)《〈雨巷〉的音乐性》,《新文艺》1929年3月号。 (4)《我为什么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新青年》6卷5号,1919年10月出刊。 (5)《柳无忌〈抛砖集〉序》,桂林建文书店1943年初版。 (6)《关于诗的一封信》,《诗刊》1957年1月创刊号。 (7)1934年11月1日致窦隐夫的信。 (8)《与元九书》。 (9)沈庆利:《写在心灵边上--中外抒情诗歌欣赏》,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年出版。 (10)《诗的格律》,1826年5月13日《晨报》副刊《诗镌》。 (11)《诗刊放假》,转引自沈庆利《写在心灵边上--中外抒情诗歌欣赏》一书。 (12)《好诗、假诗、形似诗》,1923年5月6日《努力周报》。 (13)语见《新诗:诗体重建》一文。 (14)《格律与现代---序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注释] (1)《望舒诗论》,载1932年11月1日《现代》月刊。 (2)转引自苏汶《〈望舒草〉序》,上海复兴书局1932年出版。 (3)《〈雨巷〉的音乐性》,《新文艺》1929年3月号。 (4)《我为什么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新青年》6卷5号,1919年10月出刊。 (5)《柳无忌〈抛砖集〉序》,桂林建文书店1943年初版。 (6)《关于诗的一封信》,《诗刊》1957年1月创刊号。 (7)1934年11月1日致窦隐夫的信。 (8)《与元九书》。 (9)沈庆利:《写在心灵边上--中外抒情诗歌欣赏》,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年出版。 (10)《诗的格律》,1826年5月13日《晨报》副刊《诗镌》。 (11)《诗刊放假》,转引自沈庆利《写在心灵边上--中外抒情诗歌欣赏》一书。 (12)《好诗、假诗、形似诗》,1923年5月6日《努力周报》。 (13)语见《新诗:诗体重建》一文。 (14)《格律与现代---序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全文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6-23 16:34:06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