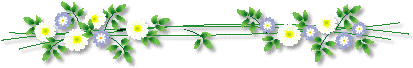英雄无名
1 一九四二年,秋。
双桥镇。
这是一座小镇,因为南北各有一座漂亮的石桥而得名。
南桥距镇上十公里左右,因为前几年发大水,石桥被冲垮,于是临时建了一座木桥。经过几年风雨的洗礼,木桥已有些陈旧。
过了南桥,就是南桥村。
村子在一座小山下面,有几十户人家。村子中间有一个宽阔的晒谷坪。坪边,有一棵高大的板栗树。黑色的枝干上没有叶子,没有板栗,却有一轮斜阳,血红的,象谁的眼睛,盯着坪里的人群。
全村一百七十三号人都来了。
栗树下面,一排站着七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
另外,晒谷坪的出入口的地方都日本兵把守,清一色的是“三八大盖”步枪,都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另外,东面高地上,还架着一挺“鸡脖子”机枪。
人群渐渐地静下来。
一个日本军官模样的人,站了出来。他腰间左系着一柄一米多长的军刀,虽然人不高,但也虎背熊腰,威风凛凛。看样子不足四十岁。
他用那双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了一遍全场。然后向大家鞠了一躬,一张嘴,竟然是一口流利的汉语,“我刚调来不久,可能有很多人不认识我,你们可以叫我武宫少佐,大日本皇军的驻本地的最高军事负责人。——请各位先静一静。——今天,把乡亲们召集起来,不是为了征粮,而是找一个人,一个与大家毫无关系的人。”他顿了一顿,“据可靠情报,昨天晚上,一个受伤的游击队员,混进了我们的村子。而且,此时就在现场。请各位把他请出来,我们马上走人。”
大家面面相觑。
半晌,武宫少佐不见有人做声,又提高了声音,“那个游击队员听着。不要心存侥幸,你就是化成一只麻雀,今天也别想飞出我的手心。——有种的,自己走出来,省得连累了乡亲。”
依然没有动静。
少佐向身后招了招手。
一个人走了出来。
那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个子不高,有些偏瘦。
人群中顿时一阵骚动。
虽然他身着一套崭新的保安团制服,虽然他的头发长了许多,而且梳着漂亮的中分头,但大家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是村大夫肖凡勋的儿子,书名叫肖征贵,因为眼角有块小疤,平辈人都叫他三疤子。他以前在镇里上班,据老大夫说,前些日子,参加了救国部队,打小日本去了。
没想到,竟然当了汉奸。
三疤子一言不发地向走过去,将人群向两边分开。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这个村不足两百人,谁化成灰了,谁都认得。
走到半路,三疤子停住了。
一个老人挡在了他的前面。
那个老人白发银须,面目清癯,正是老村长。他比肖征贵要高半个头。
“贵儿,做事要积点儿阴德。”
三疤子抬起头,看着老松树一样笔挺的村长。他的眼睛小,白比黑多,有些睡眼惺忪的感觉。他的脸比较白净,近一些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眼角的小疤,在微微地动。
“你猪油蒙了心肝了,贵儿,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老村长有些激动,明显地加重了语气,“你咋跟了日本人呢?日本鬼子占我河山,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你这是在残害忠良,为虎作......”
“叭!”
一声清脆的枪响打断了老村长的慷慨陈词。
老村长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什么。
最终吐出的是一口鲜血。
子弹打中了他的胸部。
他慢慢地倒在地上,血随即在地上漫开。
什么时候,肖征贵的手里多了一把枪。
一把崭新的驳壳枪。
人群骤然死一般地沉寂。
几乎每一个人都听到了,村口有一只乌鸦在叫。
肖征贵吹了吹枪口的青烟,还枪入鞘,继续往前面走。
这时候,他还没走到身前,人们都自觉地让开。
然而,没有几步,又有一个人挡在了他面前。
这回,是他的父亲——村大夫,肖凡勋。
他和老村长的年纪差不多大,但比老村长要瘦小的多,再加上背有点驼,所以站在面前,只有他儿子的下巴高。
“你给我站住!” 他青着脸,厉声喝道。
三疤子理都没理,伸出手去,象老鹰抓小鸡一样,一把将父亲扯在身后,一边还往前面走。
“孽种!你瞎了眼了,连老村长都杀。你把祖宗的颜面都丢尽了!今天,不准你过去!”老父亲一个跨步,又挡在了三疤子的面前。他张开双臂,和他儿子对比起来,真有点螳臂当车的味道。
三疤子伸出手去。这回,他加了些力量,只把老父亲推了一个踉跄。幸好有个人扶住才没有跌倒。
肖凡勋不依不饶,稳住身子,再次挡在路中间。
“除非,你让老子也躺下!”
三疤子依然没有说话,但脸上,没有半点退却的意思。
有细心的人又发现,他眼角的小疤,又开始在微微地动了。
全场气氛紧张起来。
人们纷纷地盯上了三疤子的手和他的枪。
——“大伯,您让让吧。”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几乎全场都听到了这个低沉而沙哑的声音。
一个魁梧的男人,什么时候,走到了老大夫的身后。
他穿着和当地的农民没什么两样,又旧又破。可是,他一站出来,却和其它人有明显地区别。具体也说不出在哪里有区别,可能是眼睛吧。他的眼睛很深,眼里有一种光,象寒冷的刀光,又象是温暖的阳光。
他拍了拍老大夫的肩膀,“谢谢您老人家。”
他不慌不忙地挤了出来。
站在三疤子的面前。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三疤子没有做声。侧身让开。
大汉慢慢地往前面走去。
看得出,他的左腿不十分得力。
三疤子让过大汉,转过身来,准备跟在后面。
这时,一只手拉住了他的衣角。
他转过来,是她的妻子小兰。
她的妻子眼睛是双眼皮,很清澈。此时,却射出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光芒来。
“你,让我很失望。”
好一阵子,大汉才走到栗树下。
阳光照着他的脸,剑眉刀唇,轮廓分明,透着一股逼人的英气。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游击队员。”他看着少佐,眼里没有丝毫的惧意。
少佐打量着他,赞许道:“是条汉子。”
“我姓吴,叫吴明。我因为受伤逃到这里来的,与村里的人没有任何关系。”
“吴明,没有名字,想做无名英雄啊?”少佐顿了顿,冷笑道,“你叫吴天明,本地游击队的队长,我们一直在追踪你。”
吴天明没有分辩,冷冷地道:“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现在就来杀我啊。我一个人杀了十几个鬼子,早就赚足本了。”
“别虚报浮夸,我们有详细而准确的资料,你只杀了五个皇军战士。——想要我杀了你啊?”少佐笑容,有了些暖意,“其实,我不喜欢杀人,特别是你这样的好汉,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
吴天明并不买帐,沉声道:“只要我活着,就一定会杀了你。”
“这样的话,我听得很多,”少佐并不恼怒,“肖征贵前些日子就这么说过类似的话,虽然他当时的口气没有你硬。”
众人的目光一齐投向站在一旁的肖三疤子。
他看着远方,白净的脸皮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我有个外号叫‘金枪少佐’,那是因为我喜欢枪。我也喜欢枪法好的人。”少佐感慨地道,“很遗憾,中国人枪法好的并不多。你是第一个。”
少佐态度诚恳,语气温和,向是在和老朋友说话。
“不是对手,就是朋友,这是我为人的信条,”少佐道,“我希望我们能合作,真诚的合作,为中国的未来,为东亚的未来——”
吴天明打断了他的话,“同你这种双手沾满了血腥的人合作,我宁愿去死。”
义正词严,不容辩驳。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比死要可怕的多。”少佐不以为然,“我至少有十种方法叫任何人改变观点和态度。如果你不相信,可以过去询问一下肖征贵。”
众人再次把眼光投向了肖三疤子。
肖三疤子脸上的那个疤子其实很小,并不影响整个面容。
吴天明也白了肖三疤子一眼,冷冷地道:“这种人,还不配和我说话。”
“那你只有回去,亲身地体会一下了,”少佐说着,挥了挥手。
两个日本兵的走过来,枪对着吴天明,示意他走。
吴天明缓缓地迈开了左腿。
其中一个兵嫌吴天明动作慢,用日本话骂了一句,踢了吴天明一脚。
这一脚力气不大,却结结实实地踢中了吴天明的左臀。
吴天明去势不稳,向前踉跄几步,支撑走到少佐身边,眼看就要跌倒在地。
人群中有的人都失声叫了出来。
然而,吴天明并没有倒下。反而向左侧身,右手一伸,握住的却是少佐左腰的刀柄。
同时,身子并没有停,顺着去势,拔出了长刀。
此时,还是没有停,顺势再向上一撩,直取少佑的咽喉。
果然不愧为游击队的队长。这一系列动作,自然流畅,快速准确,却又出乎了所有人意料。深厚的功底,过人的胆识,迅捷的应变,缺一样,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有的人在惊呼。
有的人在担心。
大多数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叭!”
就是这时,又是一声清脆的枪响,终止了这一切。
子弹从吴天明的右胸口射入的。
那把寒光四溢的武士刀,在离少佐咽喉半尺的地方止住了。
吴天明看着开枪的人,喃喃的道:“......狗.......汉奸......”
说着,他身子慢慢地倾斜,倾斜,终于倒在地上,不动了。
那把刀,跌出了好远。
开枪的依然是肖征贵。
他吹了吹枪口的青烟,把枪插入皮套。然后走上前去,跨过吴天明,捡过那把武士刀,递给少佐。
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少佐竟然还在笑。
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少佐的手里也多了一把枪,精致的,金光耀眼的左轮手枪。
这时候,人们又想起他的外号——“金枪少佐”。
他还枪入袋,一手接过肖征贵递来的刀,插入刀鞘,一手拍着肖征贵的肩膀,笑道,“谢谢你。”
生和死倒底有多远?
在村大夫肖凡勋看来,只有半公分。
等到日本人走远。肖凡勋便带着众村民,把倒在血泊中的老村长和吴天明抬到屋子里。
也许是他命硬,也许是阎王爷看他年轻,也许老天希望这个故事后面再长一些,再精彩一些,吴天明竟然还有一口气,那颗子弹竟然离他的心脏还有半公分远。而且,是穿背而出,没有停留在身体上,所以连手术都不必要。止好血清好创,只要不再受到感染,康复应该很有把握。止血清创这对于行医五六十年的肖凡勋来说,只是小儿科。
老村长死了。
肖征贵的那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左肺叶。
他死了,腰杆还是笔一样的直。
在场的很多人都哭了。
包括肖凡勋。
2 老村长的葬礼很风光,是村里近年来没有的。
因为,大家都非常自觉,都尽心尽力。特别是肖凡勋。他不仅让儿媳妇叶兰戴了重孝,而且还承担了几乎所有的费用。
第三天,上山的时候,全村人都出来为老村长送行。
大家为他垒了座宽大的坟墓,并竖了一块大石碑。上面,有两个字凿得特别显眼——“英雄”。
一切弄好了,已是傍晚时分。
最后一个离开的是肖凡勋。
只过了几天,他整个人又瘦了一圈。站在那里,让人担心,那阵山风,会不会将他吹走。
离开的时候,他还亲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按当地的习俗,平辈人根本没有必要行此大礼的,可肖凡勋似乎并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下山来,他先走回家,看了看伤在床上的吴天明。
吴天明是条好汉子,从晕迷中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一定要杀了你,金枪少佐!”这句话让肖凡勋甚至在床边服待的叶小兰倍受感动。想想自家的肖征贵的罪过,于是对吴天明照顾得更加备细。吴天明身子骨本来就好,养了几天,伤情恢复的很快,精神也很不错。肖凡勋估计最多不会超过半个月,就可以下床了。
他跟吴天明说,叫他安心养伤,不用考虑其它,伤好了,再为国家多杀鬼子,最好连他那个孽种一齐杀了。
他又把儿媳妇叶小兰叫过来,叮嘱她要好好地照顾好这位游击队的英雄,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拿出来,说游击队为了老百姓,命都不要了,老百姓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另外,他还说了儿子的事,说对她不住,叫她不要将那个汉奸放在心上,就当没有那个人了。
叶小兰觉得公公今天的嘴特别多,有些奇怪,问他是不是要出门。
肖凡勋说邻乡有一个重病人等着他去看。
说完了,肖凡勋便到里屋取了药箱,走出来。
走了几步,想了一想,又折回去,跟小兰说,在床脚的小土罐里,还有一些钱,并叫她有空的时候,去镇上称起肉回来,给英雄补充一点营养。
再走出来,他看到了栗树上的夕阳。
和那天的一样红。
树下,有几个男女在说闲话,看他走近了,大家都静了下来。
肖凡勋向大家笑了笑,没说什么。
等他走远了,那几个人又开始说了。
肖凡勋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无非是他的儿子肖征贵。
——那个孽种。
他有三个儿子,但长大成人的,只有这一个。从小,他就觉得那孩子与一般孩子不一样,特倔,又不爱说话,不爱交结。如今,村里别的和他差不多大的,儿女都成群了,而他才结婚两个月。其实,他一直也没有做过什么过于出格的坏事,而且,两口子感情还过得去。俗话说得对,“老实人做结巴事”,他不做就不做,那一做就丧尽天良。
可怜小兰这个贤慧懂理的好闺女,却摊上这样一个破落户。
有时候,他甚至这样想过,如果叶兰能跟吴天明过日子,而吴天明又是自己的儿子,那么,这一生真算是值得了。——这把老骨头偏偏没有这个命。
快到村口了,他看见一个小孩子,在路边采野花。
那是老村长的外孙女,小名唤着丢丢。她的父母双亡,所以叫这样一个难听的名字,为的是好养一些。
他又想到了老村长。两人差不多大,经常一起喝酒。死的前一天晚上,他碰到了从镇上回来的老村长,老村长打了两斤好酒,称了一块肥肉,一个劲地邀他去喝两盅。他却因为有病人,推脱了,若知道会发生这些事,那天晚上,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他也去了。
想到这里,他摸出几块铜板,把丢丢叫过来,轻轻地放进她的肚兜的小口袋里,叫她去买糖。
丢丢很开心,送了一朵花给他。
那是朵野菊花,金黄的。虽然不是金子,在他看来,此时却比金子都还有意义。
走出了村子,他停住脚步,回头看了一看。
他看到了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村子其实非常美。有竹,有树,鸟窝,有房屋,有袅袅的炊烟,还有弯弯的小路。
路上,他还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很长,而且并不象人那样躬,
村子前面,是一条小河。秋天了,河水清清浅浅。
河堤就是大路。
他走得很从容。
转了一个山坳,回头已经看不见村子了。
这时,大路和河就分开了。
大路再走几步,就是南桥,那里通往双桥镇。
河水则流向落叶潭。
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继续顺着小河走。
落叶潭是这条河水最深的地方,很少有人能潜到底。
潭上面有几棵枫树,都不大。秋天,叶子有的还是青的,有的有些泛黄,有的则已经透红了。
肖凡勋在树下站住。
他伸出手去,本想摘了一片枫叶,后来,又止住了。
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看水。
潭水蓝茵茵的。
不知是冷,还是暖。
3 又过了四天。
双桥镇。百花楼。
虽然是本地比较有名气酒楼。叶小兰因为从来没有到过,所以找了半天才找到。
兰花阁,是百花楼的雅座,在二楼。
叶小兰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浓香。既有酒香,又有菜香,还有些莫名其妙的香。
里面有三个人。
两个女人,都很漂亮,都很年轻。
一个女人,远远地,规规矩矩地弹琴。
另一个女人,在给男人倒酒。
男人就是肖征贵。
他拨了拨遮住左眼的长发,抬起头,对叶小兰笑道:“一路辛苦了,来,陪我吃点酒来。”
叶小兰心里本来就非常地不快,她留意了一下他点的酒菜,满满的一桌,尽是些平时不常见的佳肴,心里更加窝火,于是沉着脸,冷冷地道:“你过得倒挺自在啊。”
“贵客到了嘛,破点费是应该的。”
“为什么拣这种下贱地方?”
“军营不准待客,你就将就一下吧。——去拿副碗筷来。”肖征贵吩咐身边的女人道,“来,我们两口子好好地醉它一醉。”
“不用了。事情说完了我马上就走。”叶小兰没声好气地道。
肖征贵道:“有什么事?”
“你自己看看吧。”
叶小兰递过一张纸条。
肖征贵一看,上面是父亲的小楷,有些水渍,但大致上还是认得的。
肖征贵看完,问:“他怎么了?”
叶小兰眼圈红了,说话有些哽咽,“今天早上,有人落叶潭发现了他......”
肖征贵喃喃自语:“前几天都还好好的。”
“还不是因为你气得,遗信上说得清清楚楚——”说到这里,叶小兰提高了声音“——你看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了。吃喝嫖赌,杀人放火,样样俱全。你自己看看,好端端的一个家,好端端的家族名声,被你一下子全毁了。”
肖征贵倒了一满杯酒,一口饮下。然而他的脸色,并没有因此而多一点血色。
叶小兰并不甘休,“你做什么事不好,偏偏要投靠日本人——”
“别说了!”肖征贵突然道。他睁圆了眼睛,那个伤疤让他显得有些狰狞可怖。
第一次看到丈夫这样发火。但叶小兰却没有半点害怕。反而再度提高了声音:“我就要说,只允许你做的我都说不得?因为你杀了老村长和游击队长,全家在村子里都抬不起头;因为你的堕落,让爹丧失了唯一的希望,才走上那条绝路的,他希望以死来唤回你的良心。——你知道吗?当初得知你参加救国军的消息后,他高兴得都不知道姓什么了,逢人便说,说他儿子有出息,说他肖家有传统;你知道吗?你杀人之后,他几天没露过一次笑脸,也没睡过一个好觉;你知道吗,有一回半夜,他一个人起来,到外面哭。是你告诉我,他从来不哭的......”
“够了!”他大声吼道,几杯酒下肚的他,脸色更加白。
“不够!”叶小兰针锋相对,“相对于你滔天的罪行来说,这几句话远远不够!”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肖征贵缓和了一下语气,看样子,他的确在忍耐。
“呵呵,你还知道忍耐?”叶小兰冷笑道,“我说到你痛处了?你还知道羞耻了?既然知道痛知道羞耻为什么还要做禽兽不如的事?”
“我赌你再说一句,”肖征贵手差点指上了叶小兰的脸,语气中威胁的意思很明显。更重要的是,那块不显眼的小疤,在明显地抖动。
叶小兰毫不示弱,“我当然要说,你杀了我我也要说。说给所有人知道,你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你是个大汉奸,杀人犯——”
“啪!”
肖征贵结结实实地扇了叶小兰一个耳光。
他的出手很快,也很重。
叶小兰根本没反应过来,就翻倒在地。
顿时,她嫩白的脸上,现出了五个手指印。
肖征贵还在咆哮,“看不起我,你给我滚!臭婆娘,老子身边有的是女人。你滚得远远的,滚出我肖家。永远都不要回来。”
他骂得很刮毒,言语里面充满了无情肮脏污辱和讨厌。
叶小兰平时哪里受过这等委屈,又气又忿,一时说不出话来。
又过了一会儿,血从她的鼻孔里流了出来,鲜红的,还好不多。
跟着流出来的,是眼泪。
叶小兰擦了擦眼泪,站起来,一言不发地往外面走。
快到门时,转过来,盯着对肖征贵,那眼光含着泪,象两柄闪着寒光的利剑,足以穿透一个人的心。
半晌,从她洁白的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你不得好死——”
4
秋意,一天比一天浓。
吴天明,则一天比一天好。
渐渐地,虽然胸口还在痛,但左腿已经可以来去自如了。
这一天,他起得很早。
出门的时候,太阳也刚刚从后面山上露出头来。一缕清纯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象谁的目光,说不出的温暖。
对门山上,是蓝蓝的天。
天上,云不多,但都很美,或淡黄,或桔黄,或银白,慢慢地向南飘去。
“早啊,”是叶小兰的声音很脆。那次,她本想借奔丧的机会,说一说肖征贵,希望父亲的死,能使他幡然悔悟。可肖征贵不仅没有悔改的迹象,反而打了她一耳光。按平时的脾气,她会径直回自己的娘家,再也不管他肖家的事。想想刚死的公公无人安葬,想想自己在他家过去那些平安和谐的日子,再想想伤在床上要人服侍的那个游击队长,她最终选择了回南桥村——他不仁,自己不能不义。
时光似乎很容易治好一个人的心理创伤,现在的她,脸上涂满了阳光。
和阳光一样灿烂、一样温暖的,是她的笑容。
她对自己的选择很满意。办了公公的丧事,治好吴的伤,自己的心里也轻松了许多。她认为,人做善事,不一定在将来会有什么好的报偿,但一定会在当时,得到愉快的心理报偿的。
她拿着梳子,出来梳头。
“你也早,”吴天明点了点头。
叶小兰挽了个漂亮小巧的茶花髻。
“你的头发挺好的,”吴天明随意说了一句,因为态度真诚,又因为声音低沉,所以象鼓点一样,让听者的心有一点震动。
“是吗?”叶小兰笑得更开心了,她转过头去,吴天明看到了一丝羞涩的红云。
“——我的枪呢?”他突然道,“你到老村长家取了没有?”
“早取了。锁在柜子里呢,”叶小兰道,“我就知道,那是你的命根子。”
吴天明笑了笑,“你去拿一下好吗,好久没碰了,手有些痒。”
“好的,”叶小兰很快拿出来了。
沉甸甸的,也是一把驳壳枪。
她倒拿着枪管递给吴天明。
大概是有些年月了,有些脱漆。
那把冰冷的,毫无生机的枪,一到吴天明的手里,随即盛开成了一朵花。
不停地旋转着的黑色的花。
只看得叶小兰眼睛都直了。
“我想跟你学枪。” 叶小兰突然道。
“这是花动作,根本没有什么用的,”吴天明手一停,准确地握住枪把。
“不学这个,学杀人。”叶小兰很认真地道。
“为什么要学杀人?”
“为了杀人。”
吴天明笑了笑,没有再问。
“枪,其实没有什么巧,无非两个字,快和准,”吴天明想了想道,“相对于准,快其实更重要,也更难练。”
“不要教我那些理论,那些都懂,问题是现在枪在我手里,我要学枪,应该怎么做,”叶小兰很直爽。
“先练拔枪,”吴天明道。
“为什么要练这个动作?打仗的时候难道还没机会拔枪吗?”
“如果你的拔枪快到一定的境界了,就等于,你时时刻刻用枪指着对手,”吴天明道。
叶小兰仔细想了想,觉得这话很有道理。
“特别是正面的对决,出枪的快慢,几乎决定着枪战的胜负,枪手的生死。”
“我试试。”
她取过枪,插在腰间。
突然以最快的速度,握枪,拔枪,举枪,瞄准,然后对着面前的那棵桃树,大声道“给我站住,要不然就开枪了。”
吴天明笑了。
叶小兰道:“怎么样,够快的吧?”
“是比较快,”吴天明道:“你用的时间只够我拔三次枪。”
“我不相信。你来试试。”
吴天明接过枪,插在腰间,然后手张开。
“你数一二三。”
“一、二、三”
三字音未落。
枪已在吴天明手上端着。
“我没看清,再来一次。”
第二次,叶小兰依然没有看清。
吴天明作势还要来一次。
“再不能来了,别把你的伤口弄返了,”叶小兰连连惊叹,“真的不可思议。想不到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快的动作。”
吴天明笑道:“我可不是最快的。”
“还有人比你更快?是谁?”
“武宫少佐。”
“那个日本人?”
“那天,我抢他刀的时候,连我都没看清他的手里是怎样多出一把枪的。”
“那不是神了?”叶小兰咋了咋舌。
“据说,他是日本军中的第一快枪手,‘金枪少佐’的名号不是捡来的。”吴天明道,“据我们的资料,他一个人,竟然杀了四十九个中国人。其中不乏国军,八路军的用枪高手。”
“四十九个?”叶小兰咋了咋舌,“怎么那么残忍?”
“这还是直接死于其枪下的,他间接杀害的中国人,无法统计了。”
“真是个杀人恶魔!”
“另外,还有你丈夫枪法也蛮不错的。”
一听到肖征贵, 叶小兰的脸色顿时冷了下来,心里自然而然生出一种莫名的厌恶感,她讨厌“金枪少佐”都还没到这种程度,“不要提他,他现在是汉奸,是我们共同的仇人。”
“但他的出手挺利落的,”吴天明道,“这点我们不能否认。”
“他比起少佐怎么样?”
“肯定慢一些。”
“和你比呢?”
“不好说。比了才知道。”
“那天他不是在你拔刀之前,出了枪?”
“那依不得的,首先,我受了伤。拔枪别看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全身每一个部位都要十分的协调,某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动作。另外,我拔的是刀,别人的刀,别人的刀和自己的枪是完全不同的。别说刀,就是同一种枪,别人的和自己的都有感觉上的差别。感觉上的差别必然造成速度上的差别,因为,拔枪到了一定程度,完全是凭感觉的。如果伤完全好了,如果我用的是自己的枪,我估计有七八成把握胜他。”
“有不有可能,有一天,我的出手比他还快?”
“为什么一定要比他快?”
“总有那么一种预感,某一天,我们可能会在战场上见的,”叶小兰道,“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你难道还想上战场啊?”吴天明有些不以为然。
“在这种年月,以后的事,谁又能说得清呢?”
“我只知道,枪这方面的事是说不清的。” 吴天明道:“这些动作看起来很简单,有时候,也要一定天赋的。部队里,很多人都练过,但真正练到家的也不多,可是有个家伙,没见他怎么练,出手却并不比我慢多少。”
“是吗?那我有信心了。从现在开始,我天天练。你在旁边看着。开始——”
叶小兰说做就做,拉开了架势。
于是,小小的院子里,除了阳光之外,又多了许多略带磁性的男人的声音。
“手不要那么僵硬。”
“动作要连贯。”
“眼睛不要看枪,不要看手,盯着前面的‘敌人’。”
“手还要抬高一些。”
“不要发抖。”
“拔之前,尽量放松一些,若无其事的样子,才能出其不意。”
“拔枪的时候,所有可有可无的动作只会浪费时间,所以动作一定要简洁干净。”
“有的人把拔枪比喻成写诗,甚至做画。”
“这次比较漂亮,有进步。”
......
又一个深秋的清晨。
吴天明走得很快。
向北,是往镇里去的。
他是悄悄地出来的,没有跟叶小兰说。但他留了纸条,对她这些天来的关怀与照顾表示了谢意。
太阳还没有出来,晨风有些凄冷。
青石板的路上,还有薄薄的霜。鞋子踩上去,会留下一个湿湿的印子。他知道,这些印子,现在看起来这么明显,等一会儿,太阳出来,霜一化,就会不见。看着这些霜,他想到了人,活在世上时,很多人都认识你,关心你,一旦一死,你就会象霜一样,被岁月的阳光融化。
路边有水声,对岸有鸟叫,都很好听。
他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其实,他昨天就可以走的,按以往的性子,他前天就会走的,但这次,他今天才走,甚至,今天,他都不想走。
发现自己越来越舍不得离开了。
他回过头,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村子似乎还在睡梦中,静悄悄的。
偶尔的鸡啼,不时地唤起一些美丽的记忆。
在他的记忆里,开满了一种花,清丽淡雅,芬芳宜人。
——小兰,他又念及了这个亲切的名字。那个美丽而又清纯的小兰, 那个直爽而又善良的小兰,那个温柔而又倔强的小兰,几乎占据了他心里所有的位置。
她的手很白,手指很长,有些凉,有些汗,握在手里,象握着一块晶莹温润的玉。
她的腰很软,每次扶住的时候,他都担心,她会象柳条一样软倒在自己的怀里。
很多次,教枪的时候,他都想顺势将她揽进自己的怀里,不再放开。他不敢肯定,她一定不会拒绝,但他绝对有把握,让她无力也无法拒绝。毕竟是游击队长,伤好了,别说一个女人,就是三四个壮汉,他也有把握几招之内治得服服贴贴。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知道,那样做会害了她,因为自己无法给她幸福,因为彼此是不同世界的人,因为这该死的战争。
就在这几天,他发现自己老了。发现自己争强好胜的心淡了。就在这几天,他想起了家。
他希望战争快点结束,最好是就此结束。
他甚至希望摆脱,永远地摆脱,身上的这把杀人茹血的,跟随了自己多年的枪。
他很想做一个农民,在南桥村这样的村子里,盖一间木屋,找一个,哪怕比小兰差十倍丑十倍的女人,种一种田,挑一挑水,或者看一看东升西落的秋阳。
但是,做为一个成熟的男人,做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知道什么是梦想,什么是现实,知道梦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而这种差距,大多数的时候,是无法弥补的。
一个成熟的男人,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并不是为自己活的。
为了完成任务,他必须离开。
只要他还活着,只要战争还在继续,那么,他没有别的选择。
就象脚下的路,此时此地,真正属于他的只有这一条,这一条通往镇上的路,通往凶险和未知的路。
前面就是南桥。
陈旧的木色,让人担心它能不能经历下一场的洪水。
他觉得脸上有些痒了。起来还没有洗脸呢。
他下到河边,捧了捧水,洗了洗脸。
水有些冷,但很干净。于是,他忍不住趴下来喝了两口。
那种冷,一直沁到心里去了。
随着涟漪渐渐地散去,他看到自己的脸,休养了一向,竟然白胖了许多。
就在他准备站起来的时候,他看到了一朵花飘落下来。
金黄色的野菊花。
菊花是不落的,何况,又没有风。
诧异间,他的手已经搭上了枪柄。
这时,他看到了水里多了一张脸。
比菊花还要美丽的脸。
“你来了?”
“我不能来?”是叶小兰,今天穿着碎花小满襟,很合身,也很好看。
花是她扔下的。
“可以,”吴天明道,“但我还是希望你回去。”
“你呢?”
“我要去镇上。”
“不去可以么?”
“不行。我有任务在身。”
“那我也跟你一起去。”
“不行。”
“为什么?”
“因为去了,就可能回不来了。”
“倒底是什么任务?”
“杀武宫少佐,”吴天明知道自己必须说了,不然无法说服她,“因为他对我们游击队的威胁实在太大,上级命令我不惜一切代价,锄掉他。你知道,我的枪法本来就比他慢,和他对决,胜算不足三成。再加上,他身边还有个肖征贵,所以我此去凶多吉少。”
“就是死,我也和你一起去。”叶小兰对吴天明道,并不象是开玩笑的样子。
“你真不怕死?”
“不怕。”
“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中国人。”
吴天明沉吟道:“就这一个原因?”
叶小兰道:“你说呢?”
两人一阵沉默。
“我还是不希望你去?”吴天明想了想道。
“为什么你不希望我去?”叶小兰又问,感觉两个人今天话都比较多,而且说的多是些重复的话。
“因为我不希望你死。”
“为什么不希望我死?”
“因为——”吴天明突然一横心,“因为我爱你。”
叶小兰笑了。
象一朵盛开的兰花。
这时候,好象太阳出来了。
这时候,好象霜都融化了。
“其实,我们去不一定是送死,你不是说你有三层把握吗?再加上我呢。你不是说我很下苦功很有天赋嘛,你不是说我进步很快吗?其实,早就知道你有离开的一天,所以,我非常刻苦的学枪。你在的时候我在练,你不在的时候,甚至你睡觉的时候,我都还在练。你看,我的手上都起了许多血泡。我做这些为什么?就是为了有一天和你一起走上战场,杀日寇,杀汉奸啊。——相信我,我不怕苦,不怕死,我不会令你失望的。”
她望着吴天明,那恳切的目光,告诉他,冰一样纯洁、火一样热烈的心,是不容拒绝的。
吴天明沉吟不语。
他的眼里仿佛有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