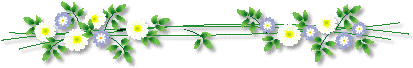新诗风初探(修改稿)
广为盛传的诗是真正的好诗。例如,唐代李绅(一说聂夷中)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和李白的《夜静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都是妇孺皆知、古今盛传的好诗。
它们好在哪里?
第一,篇幅简短,易读易记。
第二,言简意赅,明白如话。古人读之是白话、实在话,今人读之仍是白话、实在话。所以人见人爱,历传不衰。
第三,诗魂磊落,诗貌潇洒。诗魂,指立意。以上两诗的内容健康,不必多说。诗貌,指声韵、对仗、用典等等艺术手法和形式。古今诗人对此苛求完美者屡屡可见。因此,我对以上两首诗的诗貌不敢多做恭维,我在本段开头没说它们诗貌美丽,而仅说“诗貌潇洒”。我不想考证它们是否犯有宋人力避的“蜂腰、鹤膝”等八病,我只觉得它们朴实无华,没有矫揉造作。这,正是人们喜欢它的原因。且看锄禾篇,用的是平常话,说的是平常理。一个“汗”字,道出了农民的苦和累,并为下面的议论作好了铺垫。“粒粒皆辛苦”是点睛之句,既道出了劳动者的勤,又明示了消费者要俭,中华民族的两大美德昭然于五字之中,真是一字千金的绝妙白言。这首诗有两个“禾”字,会否有人把这叫做重复或叫做什么毛病呢。这不是重复。第一个禾字是写禾,第二个禾字不是写禾是写土,是写禾下的土,“禾下”仅仅是土字的修饰语而已。其实,写农民多用几个禾字又何伤大雅,总不能把汗滴到红玫瑰上去吧。再看床前篇,第三句与第二句失粘,第四句与第三句失对,是一首拗体诗。而且篇中用了两个“明月”和两个“头”字。稍作分析可知,第三句中的明月是写月,第一句则是写明月的光,明月是光的定语。至于后两句中的“举头”和“低头”,如果是当今的小人物这样写,一定会被有造诣的大人物指出:“低头似应改为低首,当否,请酌。”酌什么酌,不就一个脑袋吗,怎么抬起来叫头,低下去叫首呢?低头,谁都懂,改成低首,就会有些人不明白它的意思,何必来这个弯弯绕呢。
1976年清明时节的“四五”运动中,潮水般出现于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多数出自非诗人之手。这些诗词铿锵有力,顺口悦耳,墨泪淋漓间言我所欲言,达到了语出惊人的诗境。他们多数模仿传统诗词风格,但不泥格律,有的虽冠以“七律”、“满江红”之名,也深不以格律为然。当时流行最广影响较大的当属《欲悲闹鬼叫》,五言四句,短刃出击,是一首“感时花溅泪”的好诗。好就好在简短,情真,不矫揉造作。现在不是崇尚纯天然吗,穿纯棉衣服、吃绿色食品,人们当然也会喜欢纯天然的诗。
现在广泛流行的大众歌谣,体现了布衣才子的实力和智慧,形成了随心所欲的新形式和新风格。它们是领一代风骚、开诗代先河的民风诗!例如,“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单位没经费,喝得老婆扭脸睡……。”这些独具一格的诗苑新花,内容充实,感情真挚,没有封建色彩的金樽对月,没有小农情调的柳暗花明,诗里有家事国事天下事,有民众的愿望和怨声。这些民风诗形式灵活,风格独特,有的一韵到底,有的频频换韵,有的三句成诗,有的与外语杂用,有的风趣幽默,有的带古诗风格。这些诗都是白话村言,通俗易懂,但它们绝不属于近代白话诗。现在很多白话诗以及某些酸溜溜的歌词,或不知所云,或言不由衷,或词不达意,茫茫然如痴人说梦,除自己外没人愿看。而这些开诗代先河的民风诗,都是言之凿凿,争相传诵,与那些不知所云的酸诗迥异。
我不喜欢如梦如雾的白话诗,也不赞成今人写格律诗。格律诗词在发展过程中规矩越来越严,虽然有些规矩能增加诗貌的美容效果,但也抬高了古诗的门槛,使之难学、难写、难读、难普及,成了这类诗词慢性自杀的五尺白绫。古之学子,基本都是苦读文科,对作联赋诗颇多研习。今之学子,在学海无边的现代知识面前,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再学那些繁琐的声韵和数不清的典故。语文课上,只拣有代表性的几首古诗讲讲,略知一二即可,从不要求仿作。即使大学文科,也不过把传统诗词放在文学史中加以研讨。可是现在有些人仍在溢美和弘扬这类诗词,有的追求声律严谨,有的揣摩古人情调,甚至虚构古时的景物和感情,颇有为赋旧诗强说愁的味道。明明住在单元楼里,却要写“庭院深几许,门外一声鸡”,明明在寻找网上情人聊天,却写成“再约鹤翁话桑麻”,悠悠然摆出一副长袍宽袖的诗仙摸样。古人写诗是给古人看的,他们根据古人的眼光,按着古诗的要求去写,是理所当然的事。今人写诗是给现代人看的,为什么非要适应古人的口味、严袭古诗的要求呢。现在是乘“宝马”走高速的时代,不必再西风古道骑瘦马,坐听枯树昏鸦声。
中国古代的格律诗词是中华文化的一朵仙葩。但花开自有花落日,任何好的东西都不能永久延续。秦宫里的瓷碗,艺术价值很高,但只能做文物展给后人看,不能再批量生产,放到今人的餐桌上去。京剧如今倍受冷落,虽有名家、大腕屡屡为此国粹捧场,却总回天无力。京剧的辉煌将成为历史,它势必被新兴艺术所取代。古代的格律诗词也曾辉煌过,也是国粹,但它与珍贵的文物和精湛的京剧一样,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该画上完满的句号了。守着旧的东西不放简称守旧,对京剧的萧条和古诗词的衰落表示过分惋惜而依依不舍的人,简称守旧派。别急,我不是说你。你是保护和守护着它们,应叫保守派。
优秀的文化要继承,更要有发展。古人写诗用旧韵,新时代就该用新韵,古人讲固定的声律,我们提倡自然声律,达到节奏明快,顺口悦耳就行了,不必细究什么二四六分明。古人讲究对仗严、广用典,我们也可以学,但不要硬性规定,勉为其难。我们也可沿用古诗的篇幅样式,但不必叫什么绝什么律。有建树的古代诗人都能打破清规戒律,从不为格律的工美去剜肉补疮,而是以不改初衷保住亮点为至上。我们写诗能带些古诗的风味就可以了,万万不可把一个旧时的小圈子套在一个变大了的世界上。当然,你有写格律诗的功底,玩玩亦可。但曲高和寡,当出现无人赏花花自落的局面时,请不要说一些与您公开身份不符的粗话。
白话诗不足道,格律诗不足取。那该如何办呢?闯新路!中国诗风应该与时俱进,来个旧貌换新颜。中华诗词在历史上不断改弦易辙,历经更新换代,现在更应脱胎换骨,推陈出新。文言文改成白话文,繁体字改成简体字已获成功。诗歌已经到了开创新体式、新风格的时候了。新的诗风应力求简短明快,广纳时代语言,继承古诗风骨,不受格律限制。新的诗风应像“四五”诗和民风诗那样,有诗味,有境界,有内涵,有深趣。另外,可以参考古代的词谱创写长短句的诗。但不要标明词牌曲牌,不受原来格式的束缚,句子长短,句数多少,按需而定,自由发挥,只要读起来节奏明快,带有古词风格就好。
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著名箴言诗《自由与爱情》,在中国有两种译文。一种是殷夫的旧体诗译文: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另一种是兴万生的新体诗译文:
自由与爱情!
我都为之倾心。
为了爱情,
我宁愿牺牲生命,
为了自由,
我宁愿牺牲爱情。
众所周知,前一种译文在中国口碑流传,影响较大。因为前者译得简短明快,带有古诗风格,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后者在白话诗中算是内容充实的,也不错,但毕竟不像前者那样能使人产生一见钟情的感觉。同一首诗,两种译法,两种风格,两种效果,我们难道不能从中悟出当代新诗应具有的一些风貌吗。
我期待新诗代的到来。
2005年7月修改稿 2005年5月初稿,名《何谓好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