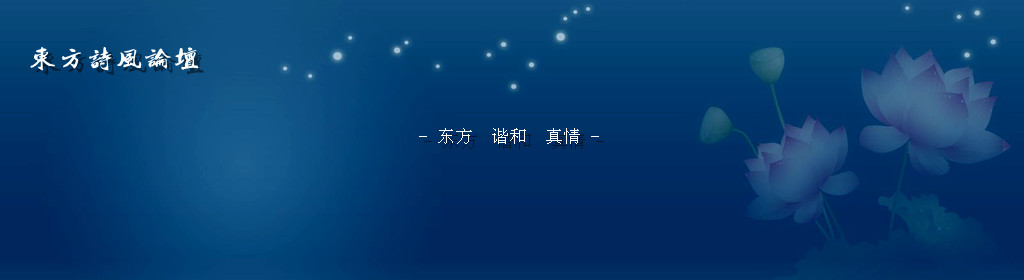刘火按:此文贴自自家今日博客。因见万兄有纺念文字,所以将此转到这里。虽不是诗,但也是一翻心境。
昨天——12月26日,是印度洋海啸5周年的纪念日。印度尼西亚各地特别是重宵区齐亚省在举行着纪念活动,以其自己的传统、风俗、礼义凭悼着五年前让海水卷走的亡灵。其中,仅齐亚省一地就有17万生灵在那场海啸成为亡灵!
这是天灾,这是我们人类自己现在还很难挽回的天灾。不过,人类在为此努力着。像不久前在哥本哈根的气候会议,世界上所有的政要都有为了在未来50年间让气候升温不超过C摄2度。——尽管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不同而发生的激烈争吵,但还是由于几个大国的妥协,最终签下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希望的那份协议。
MY GOD!
昨天——12月26日,是中国一个人的生日。那人伟大,建立起了一个不再被列强欺凌且独立的国家,并让世界政治版图在1949年重新划分。但是在他治下,却发生了1959—1961年的“三年天灾”。而现在我们知道,在那三年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生灵大约在2500万—3500万之间。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方式去凭悼过这些在那三年升天的亡灵。除了利益上的,还有道义上的,统统没有。而且最让不解的是,直到今天,就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些人,除了否认那三年死过那么多人以外,而且还经此用来说成是今天一些不安好心的人造的谣。写此文字,不是为了去纠缠旧帐,而是为了更多活着的生灵有一些纪忆。同时也为了那三年走进天国的几千万亡灵在天安宁。
MY GOD!
我的南无阿弥陀佛!
我的老天爷!
2009/12/27
附,刘火2007年写的一则有关文字:
“死亡人数增加”究竟增加了多少?
——读方志有感一
刘火
从原生的角度上讲,方志所载的历史画面大约是要比中央官修的历史要鲜活一些,也就是说,不象中央官修历史那样唯王唯圣,或不象官修历史那样,除了所谓大事件或大人物或大人物话语的干干巴巴外,方志多多少少会为它的后人留下一些历史真实的蛛丝马迹。
我出生的县叫长宁县,成文成卷成书的方志一是民国二十六版(下称旧志),一是公元1994年版(下称新志)。偶尔翻动,总有一些说不出来的感受,总是觉着哪个地方有些不对劲。现在就有这样一件事。旧志在卷十“食货”里对当时的农村是这样记载的:
“本县农村,今甚凋敝,乡间农民往往维年俱食杂粮。凶歉之时,每不得一饱。通常每百户约二、三十户,仅是自给。其他有歉二、三月食用者,有歉五、六月或七、八月者。如是者十居七、八,或仰给农事以外之劳力,以为弥补。每每衣服褛滥,室宇倾斜,民生之艰,不忍睹也。”
这段叙述,新志摘载。但其目的是想说“解放后”的欣欣向荣。确实,整个五十年代初中期,由于地改激发起了农人的生产极积性,也由于农人对连年战祸和对贪官污吏的憎恶所激发起的热情。新志载,至1957年,人均粮食也达创纪录的383公斤。不过,好景不长,紧接着的就是“大跃进”,紧接着的就是超英赶美,就是“大炼钢铁”,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于是新志在第三章“人民生活”里不得不载:
“1960年,人均产粮190、6公斤,口粮不足,导致浮肿,肿病蔓延,死亡人数增加。”
一句轻描谈写的“死亡人数增加”便把发生在长宁(也包括长宁之外的整个中国)当时的历史搪塞了过去。但历史总要留下我已经说过了的蛛丝马迹。在新志的“人口”编里有一份“1950—1985年人口指标统计表”,在这份“统计表”里对其从1957至1961五年间的记录是:
1957 全县总人口为24、88万、1958为24﹒12万、1959为23﹒65万、1960为22﹒29万、1961为21﹒79万。
在这份统计表上,我还看到,自1962年后,长宁的年死亡有绝对数一般都在2800到3500人左右,而在1959、60、61年三年间,死亡人数都在正常年份的三倍到六倍之间。1959年死亡13139、1960年死亡17176、1961年死亡9280。而1960年长宁出生的人口仅有2926,加是“三年”中的另两年,“三年”间一共出生了10376,而在“三年”间死亡的人却是39595!一个县,仅有20余万人的小县,“三年”间竟死了近4万人。这是一个怎样的死亡数字!曹树基《1958-1962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一文中说,“长宁(等)四县大饥荒五年中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合计为31‰”,而以此论为长宁等地的死亡是惊人的。但殊不知,曹文将与长宁相似的另外三县合算的结果,并不太符合长宁本身实际。从新志的“统计表”上看,长宁“三年”间的死亡是正常出生的人口54﹒96‰、74﹒76‰、42﹒10‰,自然增长分别是36﹒50‰、62﹒02‰、28﹒35‰。也就是说,长宁在“三年”间的非正常死亡要全国角度上讲,也是极为罕见的。。《筠连县志》(1998年版)记:1956,出生6583,死亡2048;1957,出生8243,死亡2418;1958,出生5531,死亡5403;1959,出生3826,死亡7503;1960,出生2523,死亡7578;1961,出生2393,死亡5559;1962,出生7257,死亡2101;从此至1985年(县志下限期)年死亡均在2000到2400人左右。可见:如果我们按描述性语言来写,那就是“饿莩遍野”。我在长宁工作期间,一位亲历者(事实上对于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人来说,我也是亲历者)对我讲,当时由于桃坪公社死人太多,多得来把死人抬上的有力气的人都没有了。于是发动机关干部下乡支援抬死人上山。为此专门制定了一个奖励政策,凡从死者家里抬一人上山埋掉,抬者每人奖励黄酒二两。我的这位文友说,作为右派分子,他在抬死人上山的支援中是立了大功的。可以想见,在那时的桃坪公社,那是一个多么暗无天日的场景,那是一个怎样的“饿莩遍野”,那是怎样的一个惨状。而我知道。桃坪公社历来就是长宁富庶的粮仓之一,而且后来我还知道,自“三年”之后的三十年间,桃坪乡(后称为乡了)的人口仍然还没有恢复到它在1958年前的人口数。
于此,岂止是一句“本县农村,今甚凋敝”了了的事。于此,岂止是一句“死亡人数增加”可以了了的事。写到这里,这则小文应是完了的时候,但是,在读着旧新两志关于民生食货之事时,还有了另一番感受。就在上文引的——也是新志所引的——那段描述后,旧志接着写道(新志未引):
“复兴农村,首在教之以智,助之以财,卫之以力。”
写完这一建议后,旧志沉痛地又写道:“诚当务急也”。但在新志第四编第三章“人民生活”中第一节“农民生活”里只写道得,“同年(1960)11月,贯彻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纠正无偿调拨生产队财物的错误。到1965年,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农民生活好转”。又在第三编“人口”里写道,“1962年,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案)》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什政策,国民经济得到恢得与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在新志里,我们看到的大都是这样的光明。倘若,我们只是从新志的一般性描述文字里去读历史,那么历史就会从这些光明的图景中搪塞了过去。而且,还会看到,我们的历史——由那么多非正常死亡的人以及他们冰冷的鲜血来填充的历史——让这干巴巴的所谓“纠正”所谓“贯彻”摭蔽了。教化,我们不说了,历朝历代都在讲教化,可是教之什么,化又化了什么,谁也说不清。而最为关键也最为重要的“护卫民力”以及及由护卫民力引伸“呵扶民心”、“关爱民生”不只是说在口里,也不是写在志里的东西,而是当历史已经过去又当当下面对未来时,让民心、民力、民生得到真正的护卫才是。阿门。
2007/2/20八米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