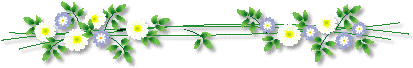| 格律体新诗的曲折历程
——略论其发展的三个阶段
万龙生
上世纪20年代,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驱,新诗无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新生事物。多年来,以政治的眼光衡量,自然是“好得很”,彩声一片。然而,新诗自己却不争气,一路颠踬前行,似乎是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孩子,越来越不得“大人”喜欢了,甚至连存在的价值、生存的.意义都屡遭质疑,其发展的前景当然更不被看好了。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耸人听闻的“诗亡论”就每每见诸舆论,“诗往何处去”成为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问题。外部的挞伐和内部的“众叛亲离”(诗人们改行和读者的离弃),两者的夹攻,确实使其深陷危机。诗人周良沛就在1997年12月9日的《文艺报》发表文章说:“有人过于情绪化地说新诗正在消亡,为此引起诗的兴与衰的争论。”
这种状况,使一切爱诗的有识之士不能不心急如焚,纷纷为其谋求出路。纠偏图变,振衰救弊,成为新诗的当务之急。两年前,在中国新诗研究所举办的首届国际汉诗诗论名家论坛上,石破天惊,提出了“新诗二次革命”的口号,并不是无的放失,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早在上世纪末,吕进就为拯救新诗提出了两条出路:一曰改善自由诗,一曰建立格律诗。这是抓住了要害,并且切实可行的。可以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形式问题是新诗的根本问题。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新诗的任务只完成了语言由文言到白话的变革,在诗的形式上是只破未立,成为一笔沉重的债务,严重地影响了她的成长与发展。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这笔巨债该到了偿还的时候。
其实,建立格律体新诗是几代诗人的理想。他们或为之大声疾呼,或为之默默耕耘,只不过在大多数时间里运交华盖,被歧视,被埋没,被打入冷宫,处于边缘状态罢了。但是她一直在顽强地挣扎,艰难地成长,恶劣的生存环境并没有使她消失,其旺盛的生命力不能不令人赞叹。经过近百年的曲折发展历程,如今,她已经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出落得像模像样,略具雏形,轮廓毕现,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是到了为其正名、争位,大张旗鼓地为其鸣锣开道的时候了。
格律体新诗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有待于诗人们继续实践,学者们继续研究,本文仅就格律体新诗的发展历史进行一次粗略的勾勒,并勾画其已有轮廓,显示其现时形态。具体地说,中国格律体新诗大体上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下文分别论述。
一、 20年代的初创
一般的史家确定,中国白话体新诗的产生当在1916年前后:新诗的两大鼻祖胡适和郭沫若都在这个时候不约而同地起步。新诗第一次发表在1918年元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四卷一期上。作品是胡适、沈伊(去人旁)默和刘半农的9首诗。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标志着新诗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时势始然,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新诗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蔚为大观,形成潮流。继胡适的《尝试集》(1921)、郭沫若的《女神》(1922)问世后,至1925年止,早期白话体新诗的重要诗人如周作人、刘半农、朱自清、冰心等相继登场,早期新诗的代表诗集如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汪静之的《蕙的风》,闻一多的《红烛》等纷纷问世,一时轰轰烈烈,似乎新诗对旧诗的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了。
但是在以胡适“作诗如作文”要求为圭臬的“诗国革命”,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的先天不足,就是决绝地割断了与传统诗歌的联系,有“白话”而无”诗”,“自白话入诗以来,诗人 大半走错了路,只顾白话之为白话,遂忘了诗之所以为诗,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 (梁实秋:《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见《时报副刊》,1922年5月29日)。在改变原来语言体系和废止原有形式体系的同时,没有建立符合民族传统的格律新体,在文体上自作多情地向散文靠拢,泯灭了自身固有的个性特征,在胡适“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片面观念指导下,诗质也不可避免地流失与稀释。这就使早期新诗丢失了作为诗歌必具的身份“认证”,因而在短暂的兴盛之后,很快就跌入低谷,面临危机,成了强弩之末。更严重的是,这也为新诗日后的发展预埋了祸根。这些严重的弊端在当时就没有躲过一些先知先觉者的慧眼。且不说来在旧营垒的攻讦,那些来自内部的尖锐批评或不同声音,也穿越时空,回响到今日。(1)
“艺国前途正渺茫”,这是1925年4月闻一多自美返国前夕致梁实秋函所附的诗句,也是对当时诗坛形势的概括。他一度“复理铅椠”,像其他一些新文化骁将一样,勒马回缰写旧诗去了。幸而在此前后,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心亡羊补牢,走上了寻求新诗格律的道路,并且卓有成效,由此开启了格律体新诗的第一阶段。
其实,在闻一多之前,就已经有人关注过新诗的形式问题(2),只不过也许因为时机未到,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罢了。到1926年5月15日,闻一多在《晨报诗镌》发表《诗的格律》,建立新诗格律的主张才得到广泛响应,并导致了新诗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格律诗流派——新月诗派的产生,成为一篇划时代的诗学文献。注意,“新月派”与“新月诗派”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详论。
史载,创办诗刊,取得阵地的想法是闻一多与“清华四子”——朱湘(子沅)、饶孟侃(子离)、杨世恩(子惠)、孙大雨(子潜)以及青年诗人刘梦苇等人在闻家客厅商定的,但是在《晨报》,创办《诗镌》则是在时任《晨报副镌》主编的徐志摩全力促成的。《诗镌》从4月1日创刊,到6月10日停刊,每周一期,共出11期,时间虽短,但是影响巨大。诗刊的出版,成为新月诗派诞生的标志;她的存在,成为格律体新诗一度繁荣到历史见证。诗刊体现了重在建设的眼光,理论与创作并重。除了前述格律体新诗的纲领性文献《诗的格律》,徐志摩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饶孟侃的两篇“音节”论,梁实秋的《新诗的格调及其他》都是对于新诗格律建设有着积极意义的佳作。至于作品,更是琳琅满目,大凡新月诗派的重要诗人尽都闪亮登场,许多堪称诗派代表作,得以传世的诗篇,如闻一多的《死水》、《春光》,徐志摩的《偶然》、《半夜深巷琵琶》,朱湘的《采莲曲》、《昭君出塞》等,也是在这里刊登的。
一个文学流派的认定,需要下列重要条件:共同的理论主张;稳固的作家队伍;自己的发表阵地;丰硕的创作成果。以此衡量,新月诗派,亦即朱自清所称的格律诗派,几点无不具备,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能抹杀的,其在格律体新诗的发展历史上,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先说理论。闻 一多把格律分为两个方面,属于视觉方面的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属于听觉方面 的有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但这两个方面又有关联:没有格式,也就没有节 的匀称,没有音尺,也就没有句的均齐。正是在视觉与听觉全面感应的基础上,闻一多提出了诗的“三美”说,即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闻氏的论述虽然囿于实践的局限,失之于简略,但是在大的原则上已经奠定了格律体新诗的基础。其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有:格律于诗的必要性,或者轻言之曰重要性;格律是什么?就是节奏;格律不是对创造的束缚,而是提供帮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律诗格律与新诗格律的区别的精辟创见(前者是千篇一律,后者是相体裁衣),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成为新诗格律建设的法宝,说是回答对格律新诗的责难的犀利武器。行内“音尺”(即音组、音步、顿)的划分,也成为新诗格律建设的基础。需要指出,对此予以重视,进行研究,而且大致同步的,是孙大雨先生。
新月派对新格律诗的倡导,是对早期白话诗“非诗化”倾向的一种反拨,扭转了早期 白话诗过于自由散漫,缺少诗味的弊端,诗人们开始高度关注诗的形式美,并在创作实 践中去尝试多种体式与格律的运用;同时,对新诗格律的多方面探讨,为我国新诗声格律建设奠定了基础,具有深远的意义。不过,如同徐志摩在《诗刊放假》中所总结的那样,新月派对新诗格律的理论探讨及其实践,也 产生了某些为人诟病的流弊。比如那些削足适履的仅仅是外部整齐而内在节奏紊乱的“豆腐干体”,尽管不符合倡导者的初衷,却也引起了读者的误解,对格律体新诗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就是闻一多本人,在实践中也没有完全解决好节奏问题。
新月诗派的创作实绩,当然首推闻一多:他无愧于“爱国主义诗人”的桂冠,其诗集《死水》也是不可替代的新诗经典。在诗体的实验上的成就,我以为应该首推朱湘他创造了许多一诗一式的“相体裁衣”的作品,《采莲曲》就是其中的典范;于十四行诗的引进,他也是功不可没。徐志摩作为主将,当然也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无须赘述。至于流派的整体成就,我想,1931年由陈梦家主编,新月书店印行的《新月诗选》尽管入选的只有18人,诗40首,却是一个精粹的缩影。而且,陈梦家的序言也是对新月诗派的一个诗意的又是理性的总结,成为研究新诗史不可不读的重要论著。1989年,是在38年之后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蓝棣之编选的《新月派诗选》,还是那18位诗人,入选诗篇却达200余首;蓝棣之的长序拨开了历史的迷雾,对新月诗派的地位与价值给予了正确的评价。令名曾受污损的先行者们九泉有知,亦当含笑乎 ?不妨指出,虽然入选的诗人仅仅18位,但是受新月派影响的诗人和诗作者,显然难以计数。何其芳和臧克家早期创作曾经受惠于新月诗派,是公认的事实。
1931年,《新月诗选》的出版,给新月派划上了一个相当优雅的句号;而陈梦家的序言则是她的一曲凄美的挽歌。因为,一种新的诗歌浪潮汹涌而至,随着1932年施蛰存、戴望舒主编的《现代》的创刊,她的道路走到了尽头(3)。
(1)余冠英:《新诗的前后两期》:“当时新诗作品漫无纪律而且粗制滥造,引起反感不少,不但守旧的人对新诗更加唾弃,即一般青年读者也厌倦了。”(1932)《文学月刊第二卷三期)这是事后的总结,再看当时的批评:
闻一多这样批评新诗的代表性诗集,余平伯的《冬夜》:“破碎是他的一个明显的特质,零零碎碎拉拉杂杂,像裂了缝的破衣裳,脱了榫的栏器具。”而且,这个评论对象“虽然是偶然捡定,但以《冬夜》代表现时的作风,也不算冤枉他。评的是《冬夜》,实可三隅反。”(开明书店《闻一多全集》第三卷)而在《女神的地方色彩》中,开宗明义就下了断语:“现在一般的新诗人——新是作时髦解的新——似乎有一种欧化的狂癖,他们创造中国新诗的鹄的,原来就是要把新诗作成完全的西文诗。”(同上)
成仿吾则形象地描绘当时新诗的状况:“一座腐败了的宫殿,是我们把他推倒了,几年来正在重新建造。然而现在呀,王宫内外遍地都生了野草了,可悲的王宫啊!可痛的王宫!”然后,他深恶痛绝地使用“恶作剧”、“浅薄”、“无聊”、“演说词”、“点名簿”、“拙劣极了”等诛语,进行拔“草”的工作,针对的都是名噪一时的名家之作。他甚至忍无可忍地斥骂:“这是什么东西?滚,滚,滚你的!”(1923.3.13《创造周报》第一期)
以上两例,都是著名批评家在新诗的高潮中所说的诤言。虽说成仿吾有酷评之名,这些话还是言之有据的。
就连极力为新诗鼓吹并担任其“祖师爷”和“辩护士”双重角色的胡适,在写于1919年的早期新诗的重要文献《谈新诗》里不但说反对新诗的人“多说新诗没有音节(当读作‘节奏’——万按)”,也承认“不幸有一些做新诗的人也以为新诗可以不注意音节”,可见其趋势之严重。
(2) 早在1920年2月和3月,《少年中国》就特设了两期“诗学研究”专号,专门讨论了诗体建设 等问题。宗白华在《新诗略谈》中给诗下了一个定义:“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 画的文字——表写人底情绪中的意境”。与此同时,田汉也给诗下了定义:“诗歌者以音律的形式写 出来而诉之情绪的文学”。(均见《少年中国》1卷 8期。)应当说,当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诗的前驱在以猛烈的炮火向旧诗营垒轰击的时候, “少年中国”的诗人们就已经在建构新诗理论的大厦了。他们要求诗必须有“音律的形式”或“音律的绘画的文字”,换句话说,他们要 求对诗做出形式方面的规定。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是陆志 韦氏。”陆志韦是早期白话诗人,他在《我的 诗的躯壳》一文中针对当时白话诗的不足,阐述了他的诗歌观认为口语与诗的 语言并非处于同一层面,口语的天籁并非都有诗的价值,有节奏的天籁才算是诗。大声疾呼:“节奏千万不可少,押韵不是可怕 的罪恶。”陆志韦的主张表明他是创建格律体新诗的前驱。
稍后,刘大白写出《中国诗的声调问题》、《新律声运动和五七言》等论文,专门探 讨新诗的格律问题,在主张诗体解放的同时,也承认诗篇并不能完全脱离 律声,并不主张诗篇中绝对不许用外形律。刘半农很早就提出要“破坏旧韵,重造新韵”,赵元任果真于19232年研制了以北平音为标准的《国语新诗韵》。
以上略举几例,其时间都在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新诗格律的系统理论之前。
(3)格律体新诗所依附的新月诗派消亡了,但是其影响并没有,也不可能消失。她成为一股潜流,一段暗香,在诗坛截之不断,挥之不去。且略举数例以存照:朱光潜于40年代出版的《诗论》所做的诗歌形式美学研究,具有格律体新诗理论基础的意义。罗念生、梁宗岱、叶公超、孙大雨等诗人、理论家对于新诗节奏继续保持着关注,还在报刊上开展过讨论。林庚,这位以自由诗登上诗坛的青年诗人,居然不听戴望舒这样的权威人士的劝阻,于1935年毅然开始了格律体新诗的实验,出版了以《北平情歌》为代表的格律体新诗集,从此,再没有改变他的诗歌方向,成为格律体新诗历史上的重要角色。而在此期间,出版过格律体新诗集的诗人还有曹葆华、李唯建、孙毓棠。此外,十四行诗移植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在40年代,冯至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四行集》,以及卞之琳的《慰劳信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10 23:56:32编辑过] |